“匹夫有责”一解
安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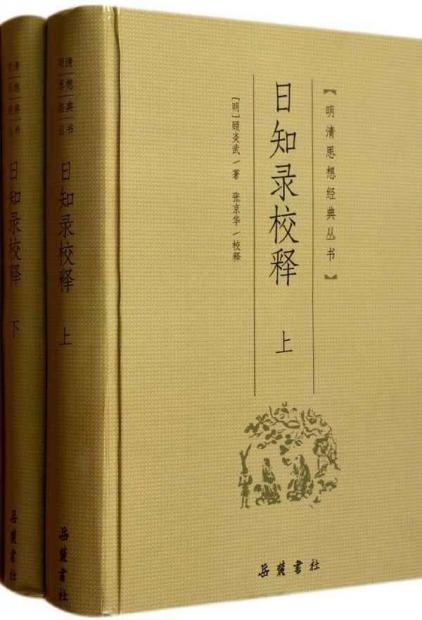
春节期间翻看闲书,读到一则清末怪人辜鸿铭的段子,内容比较深刻,性质与苏联的政治笑话有些近似。为不失原味,照录如次:
光绪壬寅(1902年),张文襄(之洞)督鄂,时方举行孝钦(慈禧)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费巨万,柬请各国领筵宴,并奏西乐,唱新乐国歌。酒阑,某忽语梁某某曰:“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曰:“君胡不试编之?”辜鸿铭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坐客哗然。(《清稗类钞·讥讽类》)
从表面看,这是清代“公知”“呲必中国”的典型恶例,矛头甚至指向了最高领袖老佛爷。从深层看,这个段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们不及深思的问题——“爱国”与“爱民”是什么关系?
毛泽东指出:“‘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1988年,P526)在“国”这个根目录下,土地、人民、主权都是子目录,而子目录是平行的。按照现代政治理论,“主权作为一种权力只能属于国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P215),任何权力的设计都不应被用于控制国民并受国民膜拜,而“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洛克谈人权与自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P283)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我放纵的特性,因此,所有权力都应当接受国民的监督。在这个段子里,慈禧太后作为主权的象征,手握最高权力,在皇权专制之下,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她并不等于国家。也就是说,爱国并不等于爱慈禧,反之,不爱慈禧也不等于不爱国。悬灯结彩,耗费公帑,豪华祝寿,巴结慈禧,不仅不是爱国,而是害国。而辜鸿铭对此提出批评,不仅不是抹黑中国,“呲必中国”,而是爱国的体现。
在上面的论述中,引用了两位西方学者的意见,但这些意见不等于西方价值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关于“国”与“天下”的看法,就体现了相似的观念。苏东巨变后,经常有人为苏联的垮台发出“亡党亡国”的哀鸣,其实,苏共变成了俄共,联盟发生了解体,物质不灭,亡从何来?在中国的皇权政治中,历代帝王都以自我为圆心,自己登基了,叫做“当国”、“坐天下”;自己垮台了,叫做“亡国”、“失天下”。皇上下台后,从不承认无德、无能和无道,反而让国民背黑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一个显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其实出于梁启超100年前的《痛定罪言》,文末确有“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饮冰室文集》卷三十三,P9)
然而,顾亭林(炎武)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756-757)顾炎武这段话里,有两个概念,其中的“天下”,与今之国家相近;其中的“国”,则相当于今之政权。在他看来,改朝换代,政权更替,不过是李唐、赵宋不同当权者的“易姓改号”而已,确切地说这是政权换班,而非亡国。二十四史里“走马灯”式的朝代轮换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这样的政权能否不被更换,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的责任,与“匹夫”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硬说有关系,无非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么,何谓“亡天下”呢?照其字面来理解,就是公平正义丧失,官员压榨百姓,彼此你死我活,社会分崩离析,这种局面才被称为“亡天下”。人们为了生存,只能奋起自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关乎“国家兴亡”,才能说“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并非顾炎武的原话,而由梁启超所概括,但他在理解上并无曲解与歧义。他的那篇《痛定罪言》,写于1915年,正值中日和议之后,因此,文中特别谈到爱国问题。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的爱国心是毋庸置疑的,“大抵爱国之义,本为人人所不学而知,不虑而能。”(《饮冰室文集》卷三十三,P5)他在文章中,以“今中国犹是中国人之中国也,未尝受统治于他国人也”为前提,设计了一组质疑问答题,“吾民曾有参政权否?”“曾否有法律以为吾生命财产之保障?”“吾民之受掊克于官吏者果何若?”等等,他的回答是无可奈何的——“余愀然无以应。”(同上,P5)在他看来,国民的爱国热情之所以受到伤害,“国民而至于不爱其国,则必执国命者厝其国于不可爱之地而已。”(同上,P5)他甚至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同上,P6)也就是说,爱国请先从高级干部做起。他在文章中引用一些国民对一些爱国的高调提出质疑,“濅(jìn)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同上,P6)梁启超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先不说“人民教育人民办”、“人民城市人民建”里的猫匿,一些将军高调廉洁,贪污国家财产黄金玉石钞票竟以吨计;一些文痞高唱爱国,竟然将妻子儿女送往敌国;一些高官满嘴马列,竟然拥有成班成排的二奶三妾。正是在他们这里,爱国与爱民发生了对立。
不过,从顾炎武、梁启超的议论里,总感到国民地位的被动与无奈。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权为民所赋,人民才是权力的主人。为防止委托的权力发生腐败与堕落,要有充分而健全的监督、制约等制度设计,而不致于非待“亡国”或“亡天下”之后,再来追究责任,分摊责任。要改变“匹夫”在“天下兴亡”中的被动处境,必须保障“匹夫”在制度体系中的主动地位,而不能总是被代表、被管理,一旦出了问题,非要从国民中找出某个“敌对势力”?
其实,品评梁启超的论述,让我想起了陈垣先生的话来,“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通鉴胡注表微》,商务印书馆,2011年,P278)假如我们模仿央视记者满大街追问“幸福”的模式,问那些遭遇强拆的拆迁户、讨薪跳楼的农民工、生活无着的失业者、开胸验肺的伤残人、城管暴打的小商贩、雪地露宿的上访者,三聚氰胺的婴幼儿父母,“你们爱国吗”?那将是一种怎样尴尬的情景?近年来,我国的一些高官、富豪纷纷将妻儿、财富转移国外,这些裸官与“外商”却在国内大言煌煌,标榜爱国,然而,这些对国家已经失去信心、根本不爱国的人们,让他们爱人民,“岂可得乎”!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