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国民性”断想
安立志
上个世纪之交,在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改革国民性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不是一个人的独奏,而是群体的合奏。鲁迅应当是最重要的一位乐手。

在改革国民性问题上,鲁迅的深刻是世所公认的,其韧性也是众所周知的。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革国民性,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与深沉的爱。相对于严复、梁启超等人,鲁迅体现了自身的鲜明特点,而这些特点并不是不可讨论的。
国民性属于精神、心理范畴,是以人为载体的。改革国民性,就有一个改革对象,即改革哪些人的国民性的问题。鲁迅要改革的对象,并非全体国民,即以最著名的阿Q为例,《论十大关系》提示说,鲁迅“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而不觉悟的农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283)此外,华老栓、九斤老太、孔乙己、祥林嫂等角色,也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主要是农民和小文人。其实,国民的某些“坏根性”,并不独体现在社会下层,梁启超在谈到当时中国现状时说,“陷中国于今日之地位者,其罪固在政府。然使政府得陷中国于今日之地位者,其罪又在国民。”(《饮冰室文集(26)》,中华书局,1936年,页8)他批评的是政府,也不为民众开脱,因为“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饮冰室文集(5)》,页18)就国民性而言,不可能只有民众的劣根性,而没有官吏的劣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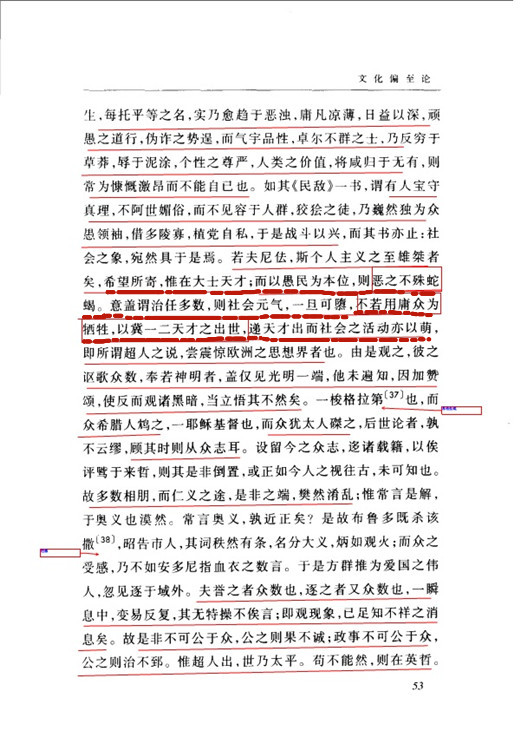
改革国民性,谁是改革者呢?鲁迅信奉尼采哲学,1907年他发表《文化偏至论》,以“天才”、“英哲”代入尼采的“超人”,以“众愚”、“庸众”代入尼采的“末人”。他是相信靠“天才”和“英哲”来改革“众愚”与“庸众”的国民性的。他这样说,“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3)“多数”是靠不住的,“庸众”可以作牺牲。改革国民性,改革者应以“天才”“英哲”为主体,“众愚”和“凡庸”只能是改革对象。鲁迅在此提出了“立人”与“人国”的概念,受到人们的赞赏。但他当时信奉的是尼采、施蒂纳的唯心哲学,这种哲学体现了“超人”与“末人”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其实是历史的局限性。
改革国民性,需要深入分析、揭示国民性,何者为优,何者为劣?何者应予弘扬,何者应予革除?然而,鲁迅的重点似乎只在于揭露其劣根性或“坏根性”(鲁迅语),这在其前期作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无论小说还是杂文都是如此,比如看客、愚昧、冷漠、瞒和骗、世故、自私、健忘、精神胜利等等。尽管他也赞赏过“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6卷,页122)但从总体说,鲁迅的笔是揭露的、批判的,其作品中的最大比重是批判“国民性之劣陋”。梁启超则指出,“无论何国之国民性,莫不各有其天赋之优点焉,亦莫不各有其天赋之弱点焉。所贵乎有国家者,国家之施政,常务利用国民性之优点而善导之,使之继长增高;其弱点则以渐矫正而涤荡焉。”(《饮冰室文集(29)》,页90)对于国民性,即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掩饰弱点,也要正视优点。

鲁迅改革国民性的手段是文学,主要是小说和杂文。他认为,改革国民精神的“第一要着”,“当然要推文艺”。(《鲁迅全集》第2卷,页439)在这一点上,鲁迅与梁启超不谋而合,梁启超也认为,国民性的嗣续、传播、发扬,“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筦其枢机。”(《饮冰室文集(32)》,页35)于是,他对国民性的揭示,主要体现为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小说)与深刻隽永的思想片断(杂文),但就其理论性与系统性而言,与梁启超的笔锋纵横、汪洋恣肆的政论风格是不同的。鲁迅的重点是揭示国民的“坏根性”,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全集》第4卷,页526),似乎切开肿块,流出脓血,任务即告完成,至于如何救治,则是他人的责任。尽管他说过,“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全集》第14卷,页410),但如何复兴,如何改善,却没有明确意见。揭示不是目的,改革需要途径,这需要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作为改革手段,梁启超强调教育,“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科立,立于教。”(《饮冰室文集(1)》,页14)胡适重视制度,“民治的制度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418)孙中山立主革命,严复针对“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之现状,建议“惟急从教育上着手”,他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页1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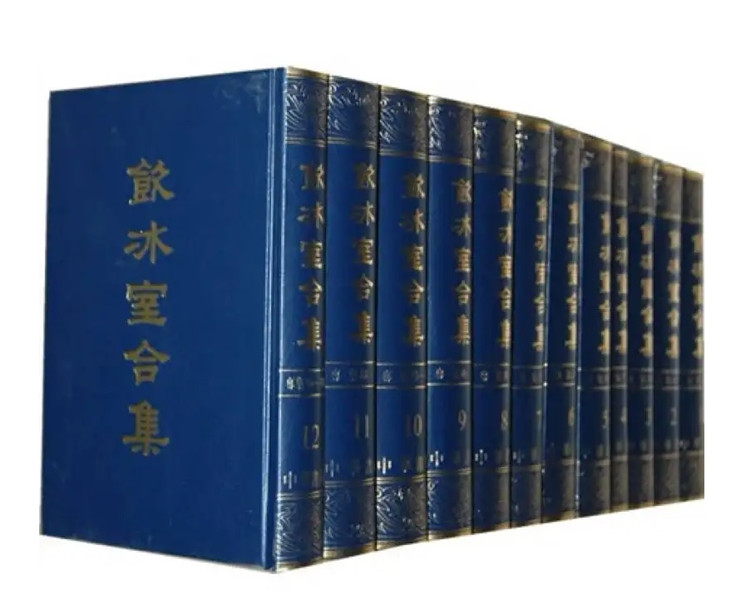
鲁迅对于国民性之批判,大约由于小说和杂文的特点所限,着重从精神、灵魂、心理方面去分析,较少从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分析原因。他到晚年认识才有所深化:“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鲁迅全集》第14卷,页410)其实,早在1903年,梁启勋就曾分析说,“一曰祖先之影响,二曰直接两亲之影响,三曰周围境遇之影响,以此三者国民性乃成。”(《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载1903年第25号《新民丛报》)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则从政治——君主专制,文化——儒家纲常,经济——生计憔悴等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国民性形成之原因。
鲁迅终生致力于改革国民性,他在呐喊,在战斗,残酷的社会现实带来的却是失望与灰心,针对“中国国民性的堕落”,他说过,“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鲁迅全集》第11卷,页40)鲁迅似乎在叹息,“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鲁迅全集》第3卷,页18)一方面,他在顽强地坚持韧性的战斗,“攻打这些病根”;一方面,他又说,“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鲁迅全集》第11卷,页41)真可谓“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其内心深处似乎有着某种孤独与悲凉。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