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以史为鉴”
安立志
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究竟是以历史“为鉴”,还是以史书“为鉴”,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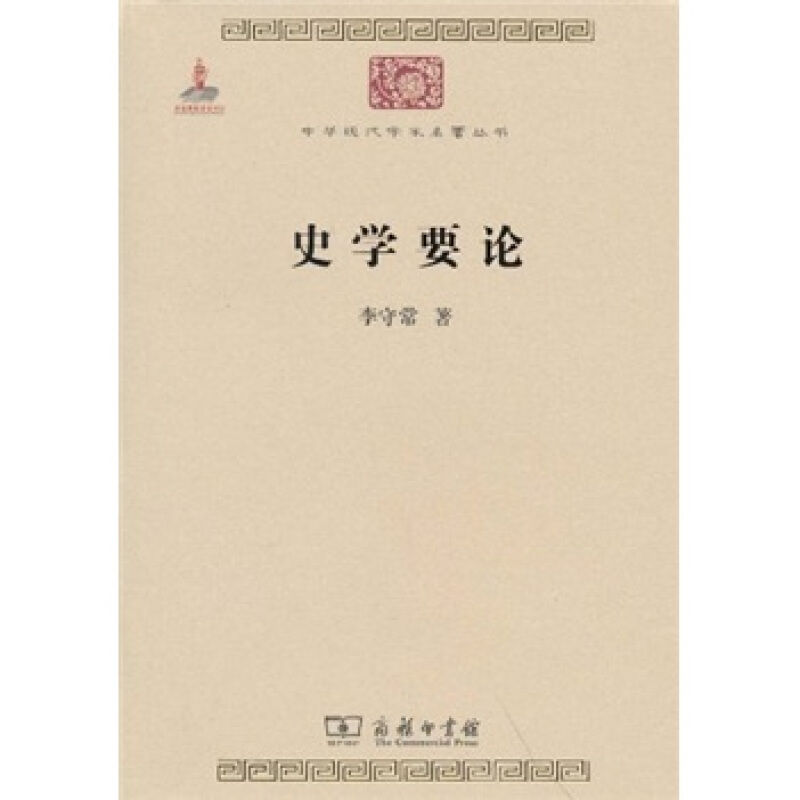
李大钊认为应以历史“为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页81-82)舍弃史书,以活的历史“为鉴”,不太好操作。活的历史在哪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在炊烟袅袅的乡村,假如千年前的历史人物还在流动,历史画面还在重现,也挺可怕的。
因此,我以为,还是以史书记载的历史“为鉴”比较方便。中国历史悠久,史书汗牛充栋,应以哪些史书“为鉴”呢?人们知道,在我国,纪传体史书以《史记》最著名,编年体史书以《资治通鉴》最权威。然而,这两部史书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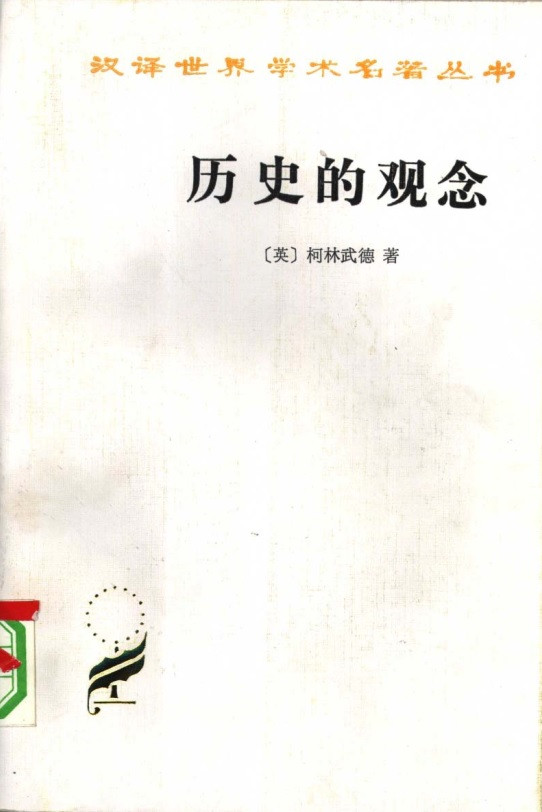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过,他又强调,“思想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前提而它又反过来成为历史知识的前提。”(《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303、319)当今世界,各种名目的主义林林总总,但以主义主导历史,历史之“足”必须适于主义之“履”的并不多见。“《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其实是“替天行道”,代天子立规矩,主义先行,观念既定,其所编写的史实,都在孔子主义的框架里,史实之“足”必须适儒家之“履”。这一方针后被汉武帝定为国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指导大汉帝国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主义。因此,所有史书的编纂都必须以这一主义为指导,编写历史是否“以论带史”,结论先行,主义是否成了“历史过程的前提”,并非史家能决定。这样的史书,已然不是历史过程的纪录,不是历史研究的结果。面对这样的历史,已经不是“以史为鉴”,而是“以儒为纲”,“以论为据”了。
在中国史学界,《史记》的地位一直很高,被称为“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首。20世纪上半叶,一个矮小尖刻的倔老头就曾将其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35)然而,就是这部《史记》,即使在当时也倍受政客与学者的诋毁与攻击,其理由就是不符合儒家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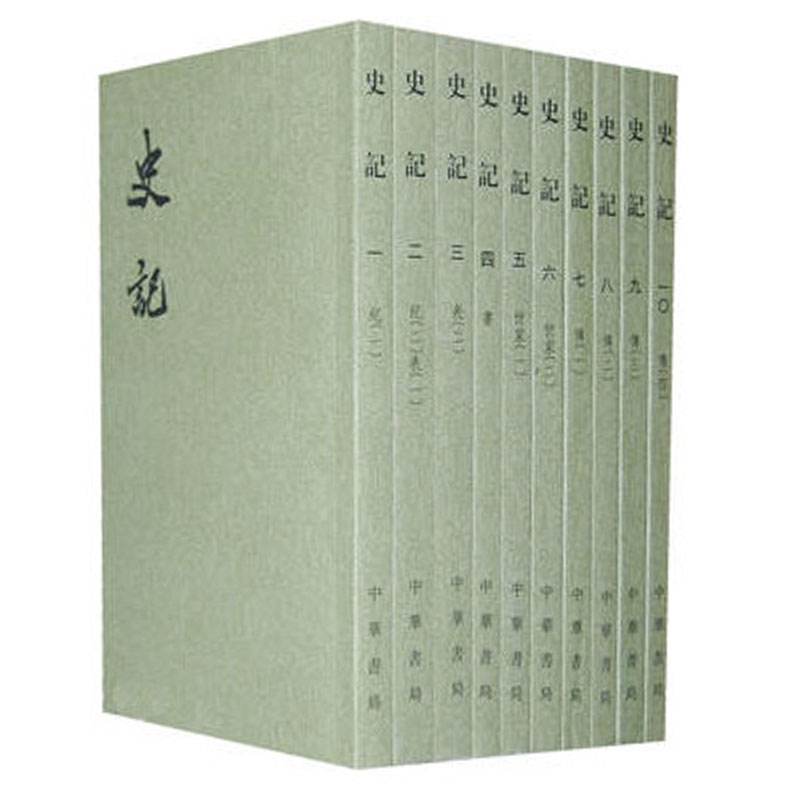
司马迁著《史记》之初,立意继承孔子的史学传统,他以《春秋》为范本,“《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汉书》第9册,中华书局,1962年,页2718)司马迁的苦心,并未得到时人的理解,反而遭到壶遂的质疑,他认为,春秋之世,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今圣君贤臣,躬逢盛世,“夫子所论,欲以何明?”面对壶遂的诛心之论,司马迁赶紧解释,“余所谓叙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也。”(同上书,页2719)
前后汉400余年,对《史记》的批评与质疑,主要指其偏离了孔子主义。西汉的扬雄认为,司马迁作《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第11册,页3580)东汉的范升也认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后汉书》第5册,中华书局,1965年,页1229)三国时蜀汉的谯周竟因为“司马迁《史记》,……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晋书》第7册,中华书局,1974年,页2142)
攻击司马迁最厉害的,却是史家同行班彪、班固父子。班彪批评司马迁修史,与上述诸人一样,指《史记》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第5册,页1325)班固则利用纂修《汉书》的机会,系统地开列了《史记》的错误,“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汉书》第9册,页2738)不特如此,他甚至从政治上批评《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文选·典引》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2158)指责司马迁利用修史,讽刺朝政,抹黑朝廷。
王允对《史记》的定性更严重了。蔡邕是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董卓死后,“王允怒其悲董卓,乃下廷尉,欲杀之,邕自狱中上书曰,欲‘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允不从,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第7册,页2006)司马迁备受屈辱毕竟修成了《史记》,蔡邕连宫刑的待遇也无缘享受,最终难逃一死,汉史当然无从修成。应当注意王允对《史记》的评价——“谤书”。“谤书”自然是对朝廷的诽谤,当然是不能“为鉴”的。

《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儒家主义的真诚信奉者,治史与从政也以儒学为规范,他指出:“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资治通鉴》第8册,中华书局,1956年,页3868)贯穿《资治通鉴》的精神内核正是儒家思想。司马光甚至通过史书为儒学来辩护。当汉宣帝驳斥皇太子“宜用儒生”的建议时,对儒家颇有微词,“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臣光曰”随即为儒家进行辩驳,他批评汉宣帝“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的说法过分了(“岂不过哉?”)(同上书第2册,页881)就是鲜明例证。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阐明了这部史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书第20册,页9608)然而,更为纯种的儒家人物,无视本书宏旨,专就细节提出质疑,重点仍然是司马光治史违反了儒学主义。这方面的人物,主要是程颐与朱熹。
程颐、程颢兄弟,同出大儒周敦颐门下,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资治通鉴》尚未告竣,程颐就想以其思想与学说干预编辑工作。
君实(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程颐)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页19)
按照他的理解,唐太宗因玄武门之变而登基,唐肃宗趁玄宗逃蜀而上位,都是篡权行为。而魏征作为太子李建成的幕僚却成为李世民的谏臣,忠臣不事二主,这分明是背叛行为,理当死罪。司马光却有自己的立场,对于程颐的见解,并未采纳。
南宋理学家朱熹,其正统观念更为浓厚。他首先对《通鉴》最初几卷“吹毛求疵”。
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1002)

他认为,尽管东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擅自称王毕竟是非法的,司马光却未予“正名”。而诸葛亮出师讨贼却被称“入寇”,这是把蜀汉当成叛乱政权。而朱熹是坚持“帝蜀寇魏”的。他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朱子全书》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22),其目的就是纠正《通鉴》本身的偏颇与缺陷。
中国古代史书,以主义为精魂,但主义的物化是权力。史家奉行主义不到位是有风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只因触怒了国君或权贵,招来杀身之祸。司马迁也不例外。正是因为触怒了主义背后的专横权力,才导致了史家的悲惨结局。司马迁修史,本欲“力诵圣德”,拍拍马屁,“以求亲媚于主上。”(《汉书》第9册,页2719、2729),然而,这个直书不隐的良史最终得罪了汉武帝。魏明帝(曹操之孙)站在皇权立场认为司马迁罪有应得,“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臣下“非贬”皇上,当然违反了主义。王肃倒是讲了公道话:“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三国志》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418)
东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范升博士左手批《春秋》,右手打《史记》,虽也知道“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然而,“稽古”与“述旧”的资源并非来自历史或史书,而是来自权力,从根本上说来自先帝,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一个重要原则——“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后汉书》第5册,页1228)立场很明确——凡是先帝怀疑的就要怀疑,凡是先帝相信的才能相信。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什么“以史为鉴”,只需要“以帝为鉴”,即以先帝对世界的看法为尺度,以先帝对事务的判断为准绳,这样的标准与圭臬一确立,什么“镜子”与“鉴戒”都无可替代。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