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德””赛”二先生
安立志

主将是谁?
五四新文化运动涌现出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每人发挥的作用不同,但对他们梁山泊式的排座次也没必要。不过,在后来的历史岁月中仍有某为“总司令”、某为“主将”的称谓,这些称谓显然体现了政治功利,倒不妨听听当事人的评价与介绍。

(陈独秀)
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后,困于贫病中的陈独秀仍然为之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后的感言》,他在文中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于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349)暮年的陈独秀回忆起当年波澜壮阔的岁月,仍然印象清晰,他态度谦抑、措词严谨,把主导五四运动的蔡、胡、陈三人称为“负主要责任的人”,且只限于“思想言论上”。韩石山不知是否以此看法为根据,他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曾有如下诠释:“蔡元培是一位韬略深远,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将,陈独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摧枯拉朽的主将,而胡适则是一位勇于除旧布新,注重建设的主将。”(见该书第二部分“胡适:我们回来了”)韩的说法很有意思,梁、陈、胡三人称谓相同,都是“主将”。
陈独秀与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是以蔡元培主掌的北京大学为平台的。正是蔡元培奉行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组织路线,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聚集旗下,从而为新文化运动完成了人才准备。
目光敏锐的读者一眼看出,在陈独秀的回忆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三位没有鲁迅。在鲁迅逝世一周年后,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开门见山:“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即周作人),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启明先生。……民国十六七年,他(鲁迅)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的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页215)这与鲁迅死后一些政治人物对他的神化,态度截然不同。可以说,陈独秀是把鲁迅“人化”而非“神化”的第一人。这是毛泽东认定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94)对其部属的评价,还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对其投稿者的评价?从陈独秀的介绍和评价来看,仅就发表文章的数量而言,鲁迅还不如他的弟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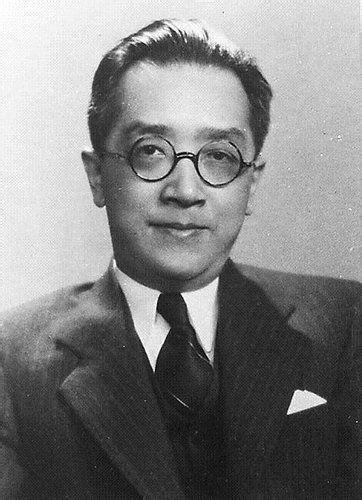
(胡适)
1958年五四运动纪念日,被鲁迅骂了一辈子的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中这样评论鲁迅:“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页172)“大将”、“健将”,又是一堆称号。
不过,“大将”、“健将”,毕竟还不是“主将”,对此鲁迅有清醒的认识。1922年12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坦承,“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全集》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41。以下同书只注页码)鲁迅笔下的“那时”是指新文化运动时期。从鲁迅口中的“须听将令”、“那时的主将”,可以看出,鲁迅是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并非主将。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除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外,还涌现了一批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等,这个群体不同于等级鲜明的军队系统,他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毕竟是不同的。
“德先生”与“赛先生”
当代官方史书和教科书有一个权威结论,五四运动是以“民主”与“科学”作为旗帜的,当时的人们热烈呼唤“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从而构成了五四运动的核心价值。那么,在当时,“民主”与“科学”,或者“德先生”与“赛先生”,是谁提出来的呢?一般认为,率先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是陈独秀,而积极与之呼应的则是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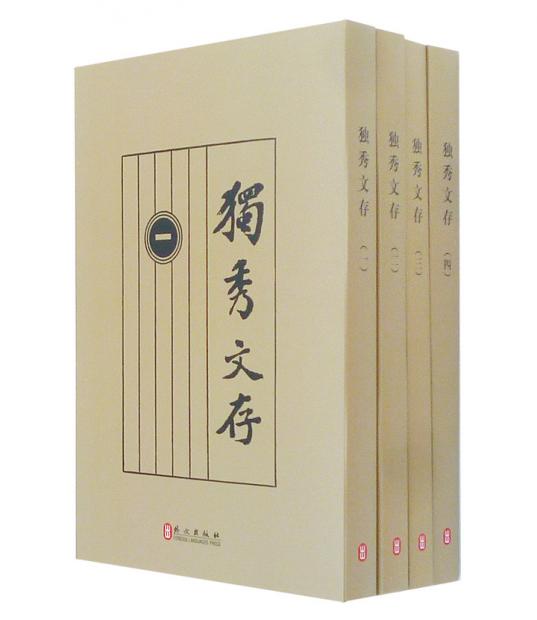
1919年1月15日,时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独秀文存》卷一,亚东图书馆,1922年,页362)这是五四时期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打出“民主”与“科学”旗号的最早出处。陈独秀接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上书,页363)可见其立场之坚定。

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文中指出:“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接着,他转述了陈独秀的那段话:“陈先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书店,1930年,页151-152)
鲁迅对此是什么态度呢?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其前身名为《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此时的鲁迅,作为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公务员,对新文化运动并不热心,无聊苦闷之余,几乎每天在绍兴会馆里抄古碑。及至钱玄同造访并规劝,才答应为《新青年》写文章。1918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就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这段经历鲁迅自己清楚地记录在《呐喊》自序中。从鲁迅作品中查阅,似乎并无“德先生”、“赛先生”这样的字样,不过,这并不等于鲁迅不曾涉及民主与科学的问题。
鲁迅与“赛先生”
鲁迅对科学问题即“赛先生”的态度总体是正面的、积极的,但却有所保留,有所疑虑。鲁迅的《科学史教篇》写于1907前,比五四运动早了10余年。顾名思义,这篇文章即以科学为主题。稍晚一些的《文化偏至论》,因为确定了“掊物质而张灵明”的主题,自然也有大量篇幅涉及科学。五四时期的《随感录三十三》,1933年的《电的利弊》,也谈到了科学问题。这四篇文章,大概是鲁迅集中议论科学问题的作品(鲁迅早年的《说鈤》、《中国地质略论》等及分布在其他文章中的散论,本文未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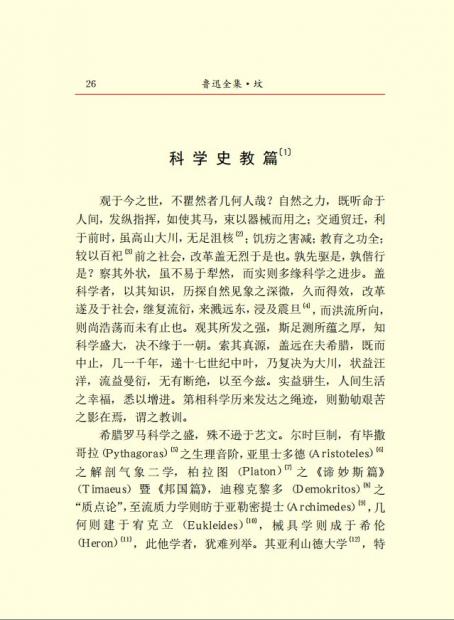
(一)思想自由的肯定
鲁迅早年赴日留学,学得是医学。医学自然是科学门类之一。鲁迅对科学并不陌生,他对“发现”与“发明”就有明确的区分,“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发现),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页314)科学的发现与发明是自由的产物。政治与法律层面的自由自然为前提,自由首先是心智与思想的自由。奴隶地位、禁锢状态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出成果的,即使砸上500亿也未必能造出高端芯片来。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首先从路德的宗教改革谈起,他以近乎《共产党宣言》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吻高度赞颂因宗教改革出现的新气象——束缚松弛,思想自由,社会无不出现新的起色,于是就有了哲学上的新发现,科学技术的新发明。以此为开端,成就了许多新事业,如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改善了机械动力,发展了文艺,拓展了贸易,如果不是去掉束缚,释放人心,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鲁迅的原文是这样:“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页48)鲁迅的话是有道理的,想想欧洲宗教法庭对布鲁诺、伽利略的迫害,可知此说不谬。
(二)自然科学的倡导
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虽然把科学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看法还是积极的,“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页35)鲁迅并非止步于抽象肯定,他下面的论述则比较具体,“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孰先驱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页25)如同今日的“科技”概念一样,当时同样“科学”“技术”不分。鲁迅对科学的肯定与支持,当然反映了时代趋势。正如胡适1923年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所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52)这样来看,鲁迅对科学的强调并不奇怪,时代使然。
(三)科学实业的结合
鲁迅对于科学与实业二者关系的论述是有现实意义的,“故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页33)他在当时就已认识到,科学与实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由此他提出了“物质文明”的概念,“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亦即胚胎于是时矣。”(页32)正是由于科学与实业的结合,从而促进了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经济发展,给普通民众的生活甚至军事国防带来了直接的利益,他指出,“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数其著者,乃有棉铁石炭之属,产生倍旧,应用多方,施之战斗制造交通,无不功越于往日;为汽为电,咸听指挥,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页49)其中,就提到了矿业、纺织、交通、国防、人民事业等诸项。
(四)科技滥用的批评
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初衷都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文明。然而,在一些政权与政客那里,科技的发展,不仅悖离了这些初衷,反而给人类造成了祸害与灾难。鲁迅生活的年代还没有原子弹,但他在《电的利弊》中就对电刑提出了尖锐批评,“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鲁迅全集》卷5,页17-18)
但在另外一些领域,科技的进步不是用来促进社会的文明,而是用来传承和发扬古已有之的陋俗与弊端,或者维护僵化、守旧的制度。鲁迅下面这段话曾广被引用,几乎成为抨击这个“染缸社会”的独门利器,他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同上书,页18)指南针、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两种,其用途在国内外天差地别。鸦片是外国输入的毒品,竟然成为中国民众的生活必需品,这也是林则徐始料未及的吧。联想到当今的互联网,政客建立“绿坝”,流氓诈骗钱财,这也许是互联网的发明者想象不到的。最先进的科技往往开发出最落后的用途,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
(五)物质主义的多虑
科学与实业的结合,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涌流,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与此同时,他又担心科学发展会带来“物质主义”,“不知纵令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则按其究竟,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页54)对此,他不免忧心忡忡,“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页54)
鲁迅对科学进步的困惑,对物质文明的担忧,他的看法有代表性,且产生较早。在该文发表10年后,梁启超访问欧洲并撰写了一篇《欧游心影录》,就表达了与鲁迅极为相似的心态。在这一问题上,倒是胡适表现了更为理性与长远的眼光。他批评梁启超,“很明显地控告那‘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欧洲全社会‘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养成‘弱肉强食’的现状,‘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他很明白地控告这种科学家的人生观造成‘抢面包吃’的社会,使人生没有一毫意味,使人类没有一毫价值,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叫人类‘无限凄惶失望’。”(《胡适文集》第3卷,页154)他认为,在中国的科技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上,还远远谈不到担忧科技发达与物质主义的程度,“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同上)胡适写于1923年的观点对于鲁迅1907年的看法有无意义呢?
(六)脱离国情的杞忧
《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多方征引外国思想资源,甚至对尼采、叔本华、施蒂纳、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崇有加,然而,他却对国内一些人士引进外国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极力反对,“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作之前鉴。……且使如其言矣,而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页46)从字面来看,他一枝劲笔横扫了一片人,其中至少包括梁启超、严复、王韬、郭嵩焘等人,最直接的批判锋芒直指近代以来的洋务派从国外引进坚船利炮、铁路电话。然而,在当时情况下,相对于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清廷保守官僚,毕竟体现了这些洋务派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当然无法避免时代的局限性,然而,有谁能说作为洋务派思想先驱的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是代表了当时的进步精神?
胡适在批评梁启超的看法时,曾经这样说,“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胡适文集》第3卷,页154)鲁迅并非梁启超,鲁迅担忧的是中国也非西欧。当时的中国,并非科学进步、经济发达的西欧,在一个经济落后、科技无多、民生凋敝的国度,奢谈“物质主义”、空论“物欲来蔽”,这样的看法,不是超越阶段,而是无视国情,倒是真有点“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的况味。
(七)唯物史观的欠缺
读过《文化偏至论》的读者都知道,鲁迅当时推崇的西方哲学思想是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和施蒂纳的唯我论等等。这些思潮都是唯心主义。鲁迅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坚持,表现很鲜明,他强调,“主观主义者,其趣凡二: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页54)不分要以“主观为准则”,而且“主观之心灵界”较“客观之物质界”——“尤尊”!“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为,亦可弗问客观之结果若何,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焉。”(页55)在鲁迅这里,“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根本没有“客观基础”、“实践标准”的位置。由此可见,鲁迅提出的“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针,体现的正是精神与物质的错位,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说明他在世界观上信奉的是唯心主义,而非唯物史观。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778)鲁迅“掊物质而张灵明”(页47)的思路显然背离了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思维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也知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页2)即使是管仲,也不会认为“礼节”先于“仓廪实”而产生,“荣辱”先于“衣食足”而滋长。
鲁迅与“德先生”
鲁迅在著作中不曾提及“德先生”,也从未给予“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以肯定与支持,但并不等于他从未提及“民主”,《文化偏至论》中“民主”至少提到三次,不过,从上下文来看,这并不是对于民主的肯定与推崇,往往是为其否定民主的论述进行铺垫。与“掊物质而张灵明”相并重,在民主问题上,他坚持“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针。“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当然要涉及人群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且主要指个人与群众的范畴。鲁迅多次提及两组概念,一组是“超人”、“天才”、“英哲”、“雄桀”、“智者”等;一组是“众庶”、“多数”、“凡庸”、“众愚”、“庸众”等。这两组概念也是两类人或人群。鲁迅在1925年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鲁迅全集》第11卷,页470),那么,“改革国民性”的主体与对象是谁呢?或者说,谁改革谁呢?“众愚”改造“众愚”显然不可能,是“英哲”改造“众愚”呢,还是“众愚”改造“英哲”?鲁迅显然认为,应当由“英哲”改革“众愚”。那么,鲁迅在这两群人中又属于哪一群呢?可以确指的是,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华老栓等等显然都是“众愚”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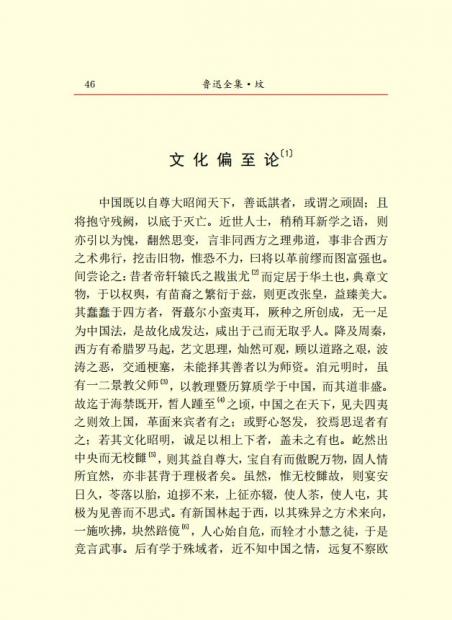
(一)关于“多数”“庸众”
按照传统理论,英雄史观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宣扬英雄人物创造历史。人民史观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前者是唯心论,后者是唯物论。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有多处评价民众与多数的言论,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他批评那些歌颂民众的意见,“彼之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盖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页53)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基于他本人对民众这个群体的判断,“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页52)“伧俗横行”、“沦于凡庸”当然不是好话,他下面的比喻就更加不堪了,“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食欤?”(页58)他把天才与群众的关系,比喻为人与猴群的关系,从而否定“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多数治理”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多数民众成了树上栖息的“群猴”(“木居而食”的“众禺”)。猴子毕竟是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的近亲。那么,把群众等同于“至劣之动物”是否更加过分?“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页52)“盲瞽鄙倍之众”被视为“至劣之动物”;于是只能“主我扬己”以“尊天才”。看来这天才就是“我”与“己”。
(二)关于“天才”“英哲”
主观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由少数英雄人物的意志、品格、才能决定的,认为人民群众不过是消极、被动的“惰性物质”,是少数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随者。鲁迅在本文中大力赞美的叔本华(主张“生命意志”)、尼采(主张“权力意志”),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在《科学史教篇》推崇的嘉莱勒(卡莱尔)是西方哲学界“英雄崇拜”的始作俑者。卡莱尔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05年,页1)英雄史观在德国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基础,鲁迅十分钦佩的尼采就认为,“超人”是历史的主宰者,没有“超人”就没有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奴隶”和“畜群”,是“超人”用以实现其意志的工具。鲁迅在本文中明确指出:“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页53)“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页53)他把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超人”和“大士天才”身上,即使“大士天才”不可得,退而求其次,“英哲”也可凑合。“以愚民为本位”,不仅仅是“恶之不殊蛇蝎”,一当“治任多数”,整个社会的“元气”就会丧失。正因如此,倒不如把“庸众”当作供桌上的牺牲,作为“天才”出世的学费与代价。
(三)关于一导众从
“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页54)鲁迅的说法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古往今来,一些大号人物,往往以“导师”自命,“领袖”、“统帅”、“舵手”则是“导师”的同义词。“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页54)这里的“置”有“放弃”“弃置不用”之义,“置众人而希英哲”,抛弃民众,寄望英哲,这像话吗?“一导众从”意味着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一导众从”,公共治理、政务公开自然不需要了,“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页53)岂不是公然主张黑箱操作,暗室政治?不过,这样的思路与寄望于“明君圣主”、“清官贤臣”根本没有区别,这与《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也完全是另一种思路。

鲁迅告诉许广平,“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鲁迅全集》卷11,页467)在“现在”与“将来”问题上,“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其中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同上书,页466)他是一个“轨道破坏者”,且“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至于建设,那是没有的。他承认自己没有“一导众从”的能力,“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同上书,页460)那么,鲁迅这“一导众从”的方针如何实行呢?鲁迅对民主充满了误读,在其后的著作中,他既不曾谈及“德先生”,也不曾谈到民主,一直到30年代他成了左翼文坛的领袖之后,在茫茫的政治海洋上,才忽然发现了灯塔,那就是苏俄模式。于是他多次撰文,赞美苏俄、维护苏俄,“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鲁迅全集》卷4,页436)1933年,他甚至撰文为苏俄暴力统治辩护。对苏俄文化总管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剧中人指责苏俄政权“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的说法进行驳斥,他甚至对“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表示赞同。(《鲁迅全集》卷7,页421)庆幸的是,他的“一导”与后来的政治趋势是一致的,可悲的是,“众从”的结果却是悲剧。
(四)关于人人平等
美国《独立宣言》中有:“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页26)鲁迅对于民主社会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人人平等”,并一直为此而困扰。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多次表示这种担心:“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页49)“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页51)“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页52)他批评民主政体“夷隆实陷”,意思是社会机制的绝对平等主义。“夷隆实陷”近于削峰填谷、截长补短、去高就低、杀富济贫。这就是鲁迅所担心的“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荡无高卑”、“夷峻而不湮卑”。这实际上是鲁迅对民主机制的陌生与误解。鲁迅没到过民主国家,不了解民主政体。在自由民主的机制下,法律上的人人平等,并不否定每个人在天赋和能力上的差别,同时也尊重每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在自由民主的机制之中,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创造知识财富,以实现多姿多彩的人生价值,这就是这类政体之下之所以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
(五)关于多数暴政
鲁迅对民主机制的另一担心就是“多数暴政”。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他多次指出,“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页46)“借众陵寡”,如同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甚至“烈于暴君”。他进一步指出:“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页47)“多数治理”如同“千万无赖”管理社会,比古代的“独夫民贼”更为可怕。“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页49)鲁迅不知道,“同是者是,独是者非”,这恰恰是独裁政治的特征。
有人说,鲁迅关于“多数暴政”的论述,体现了超前思维和预见性。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其实,亚里士多德、杰斐逊、柏克、贡斯当、托克维尔等多位古代西方政治家或著名学者都曾有所揭示,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平民“不以‘法律’为依归,就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页191)美国开国领袖杰斐逊则指出:把“全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集中在同一些人手里”,“173个暴君肯定和一个暴君一样地富于压迫性。”(《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29)
鲁迅的上述论断客观上对我国的民主建设起着消极作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国民众只经历过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页225)在一群奴隶从来不知“人民主权”、“多数统治”为何物的国度里,片面强调“多数暴政”是十分奢侈的。这如同灾民告诫富翁肥胖有害,太监劝谕皇上纵欲伤身是一个道理。
(六)关于民主本质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鱼龙混杂地引介了许多外国学说,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即为其一。这个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毁灭性批判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主张极端利己主义,把一切外在约束如政府、法律等均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鲁迅欣赏的主要是他的“唯我论”。鲁迅指出:“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页52)在他看来,无论君主制、民主制都是专制;卢梭的“公意”,国家的法律都是束缚。那么,鲁迅要的是什么呢?“任个人而排众数”,也就是“立人”。那么,如何“任个人”或“立人”呢?那就是“自觉至、个性张”,于是“沙聚之邦”,“转为人国”。(页57)何谓“自觉至、个性张”呢?鲁迅的标准是,“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页52)这与施蒂纳其人的“估价、评价任何东西都不会大于、高于其自身,简言之,因为他从自身出发并‘返回自身’。”(《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页176)何其相似乃尔!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