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目的手段论”与
马基雅维利主义
安立志
经历过全民学哲学的年代,对“三规律、四范畴”印象较深。目的与手段大概也属哲学范畴。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上,中外思想家有过许多论述,最典型的就是对于“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主张或否定。鲁迅是这一观点的主张者。

“目的证明手段正确”是否正确,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笔者无力阐述,只是在本人的阅读范围内,列举相关思想家的一些论断进行对比分析。曾有名言曰,“有比较才有鉴别”,马克思也把“分别研究”“加以比较”,作为“理解这一现象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页131)这样的对比终归是有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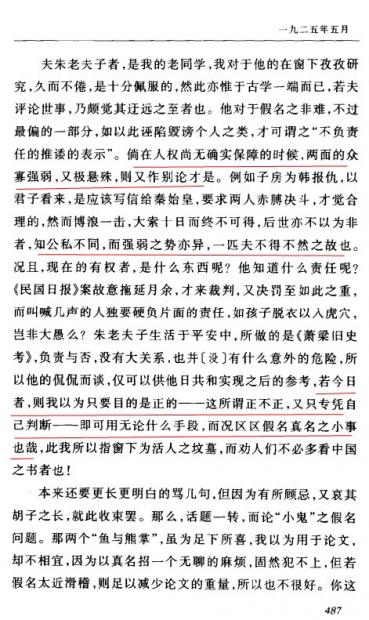
1925年5月3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87)当时,许广平还是鲁迅的学生,这封信后来收入《两地书》,当然不应视为他们的通信隐私。正因为是通信,鲁迅才会在抒发其思想立场时,较少顾忌而直抒胸臆。“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这与“目的证明手段正确”逻辑如出一辙,即只要目的是正当的,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选择的;换成这样话也不是不可以——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如何确定“目的是正的”呢?鲁迅的行文很明确——“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也就是说,我的目的是否正确,只能我自己说了算;或者说我个人的主观认知和自主判断,才是我的目的正确与否的根本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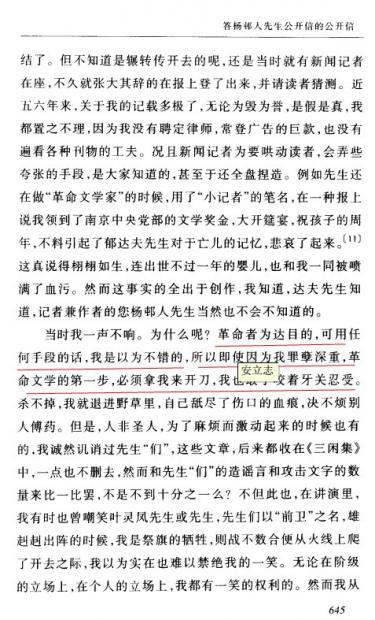
鲁迅这封信写于1925年5月,8年半之后,1933年12月,鲁迅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写道:“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鲁迅全集》第4卷,页645)给杨邨人的公开信,强调的是,“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鲁迅显然认为,革命者的目的都是正确的,既然目的正确,就“可用任何手段”,而且他认为这一点毋庸置疑——“我是以为不错的”。鲁迅的话,换成当今某种学术语言,也可以这样说,追求实质正义,毋须考虑程序正义。
从1925年到1933年,在这8年多的时间内,鲁迅的经历很曲折,也很丰富,其中一个重大转折,是他在1930年初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阅尽世事的鲁迅,“目的证明手段正确”,1925年这样说,1933年也这样说,这说明他的观点,如同外交部发言人的习惯用语,是明确的、坚定的、一贯的。不要以为笔者引述的原文使用了省略号,就会有违鲁迅的原意。在这里,我首先声明,此处删掉的只是与主题无关的文字,决不影响鲁迅思想的完整性。我再次指出,凡引述之处,均已对原文出处(甚至页码)作了详细标注,倘有置疑,可以随时查证。

人们通常认为,“目的证明手段正确”是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发明,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有人从其代表作《君主论》中概括出一句名言——“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然而,翻遍《君主论》全书也没找到这句话,倒是在该书第十八章看到这样的说法:“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86)不过,在马基雅维利另外的著作中看到了类似的论述:“为祖国的安全尽心尽力的人,不应该考虑正当或不正当、慈悲或残忍、值得赞扬或该受羞辱,而是应该把所有顾虑摆一边,完全遵照可以求生保命和维系自由的策略。”(《论李维罗马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页433)由此可见,“目的证明手段正确”这一命题,在马基雅维利手里,竟然变成了政治哲学,从其论述里可以看出,他的确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如果爱国,就可以奉行“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哲学,这样的爱国值得肯定吗?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在黑格尔看来,手段自有其独立品格,手段的地位并不低于目的,手段不过是一个“外在于”目的的“中介”与“客体”,手段的性质无须目的来认定。因此,目的的善良无法为手段的卑鄙来辩护,目的的正确也无法为手段的荒谬来论证。从鲁迅“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无论什么手段”的看法中,总会产生一种感觉,目的是主要的,手段是次要的;目的是主导的,手段是从属的。因此,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从目的。这些看法至少在黑格尔这里找不到理论根据。黑格尔这样说,“手段是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逻辑学(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页437)为了强调黑格尔这些论断的正确性,不要丢下列宁的断语。列宁在黑格尔这些引文之处写了旁批——这是“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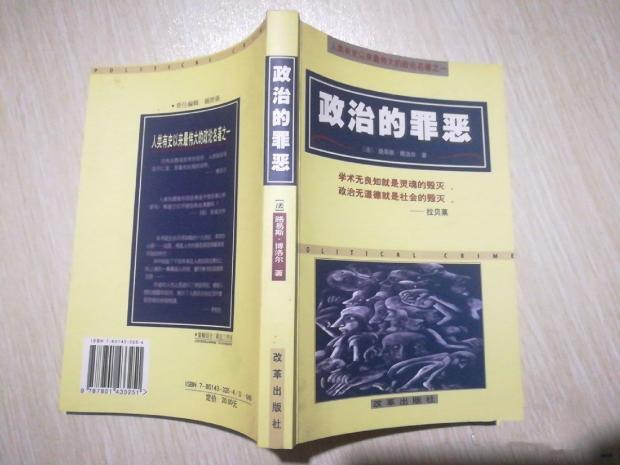
法国学者博洛尔专门著书论证政治带来的种种罪恶。他指出:“政治必须对下列危害极大的格言在实践中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负责,这些危害极大的格言就是:‘强权大于公理’、‘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公共安全是最高法律’。没有哪一次政治犯下的罪恶不是以国家理由为借口来企图证明其为正当的,也没有哪一次国家理由不是合理的。”(《政治的罪恶》,改革出版社,1999年,页4)本书作者路易斯·博洛尔的生平不尽了然,从版权页上只能看出,该书是“根据伦敦费希尔·安文出版公司1898年版译出”。这从书中主要列举了拿破仑、罗伯斯庇尔等人的事例判断,这应是一部19世纪之前的作品。
考虑到这一章的标题《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主义》,可以确知,他所概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或“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但是,他又公正地指出:“马基雅维利主义并不是产生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创造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内容都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身上所看到的东西。”(同上书,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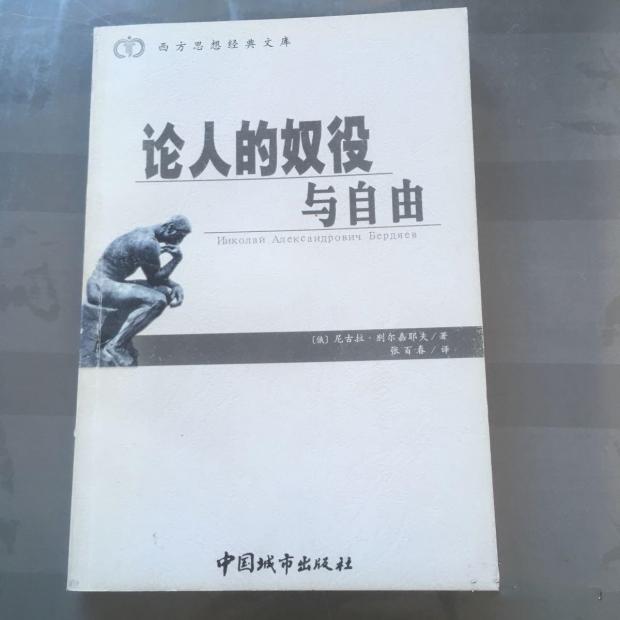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沙皇时代已经声名鹊起,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他被驱逐出境。他的后半生长期侨居法国,但却获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作为信奉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他对目的与手段也有过明确论述,“充满人类生活的正是手段,并且是不道德的手段,在生活道路上人们忘记了目的,而且,说实话,目的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它完全是抽象的,是分裂的结果。”(《论人的奴役和自由》,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页167)他就“目的证明手段正确”这个命题举例说:“国家总是利用野蛮的手段,如特务活动、谎言、暴力、杀人等,区别只是程度不同。无可争议的是,这些手段是十分不道德的,但它们总是被良好的和高尚的目的所证明。关于这个目的的质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仿佛是良好的和高尚的目的从来也没有被实现过。”(《论人的奴役和自由》,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页166-167)一边是“良好的和高尚的目的”,一边是“十分不道德的手段”,不仅前者“从来没有被实现过”,而且后者却被前者“所证明”,真是入木三分的讽刺。恰恰在这一点,他与法国学者博洛尔形成了共识。

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原本是哲学问题,但在社会生活中,它更多地表现为道德伦理或社会政治问题。英籍奥裔经济学哈耶克曾经这样说:“‘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徳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徳的否定。而在集体主义的道徳里面却成了必然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决彻底的集体主义者一定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的利益’的话,因为这个‘整体的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141-142)哈耶克是个有争议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我国的学术氛围中,由于其对于计划经济的深刻解剖与批判,有人称其为“乌托邦的掘墓人”;由于其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概念的混用,有人称其为“资产阶级的敌意”。尽管如此,我国学术界引进其学术思想,对于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非无益。哈耶克这部著作我看到三种中文译本,王明毅等译本、滕维藻等译本和台湾的殷海光译本。滕本是1962年的“内部读物”,只是感到译笔较好,因此作为引文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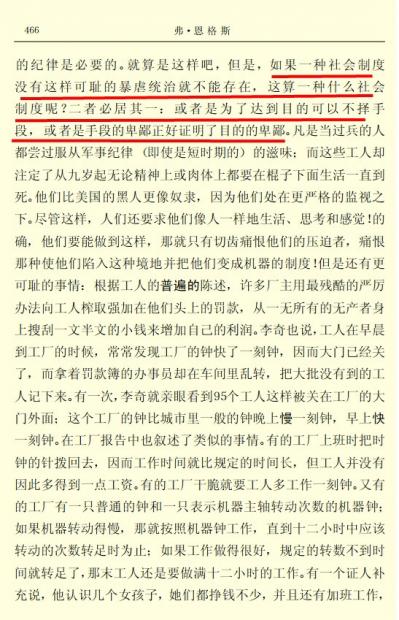
不要以为否定“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对这种学说嗤之以鼻。恩格斯的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出版,比《共产党宣言》还早两年。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深入解剖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制度,他指出:“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页466)在恩格斯看来,不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恰恰相反,却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这体现的正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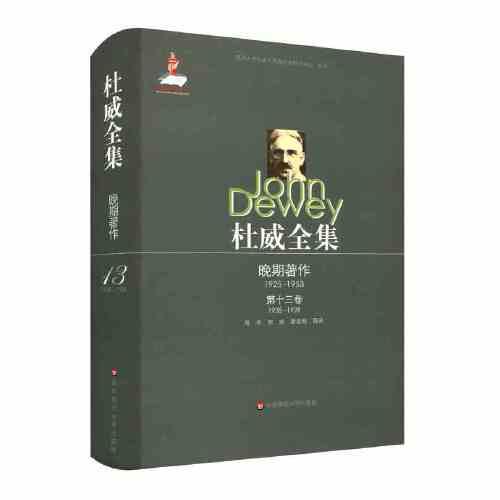
鲁迅在1920年代就开始译介托洛茨基的文学论著,是托洛茨基文学思想在我国最早的翻译者。托洛茨基是早期苏俄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也是苏俄政权内部斗争的失败者,他被驱逐出国后,仍未逃脱被暗杀的厄运。托洛茨基作为曾经的革命家,流亡期间出版了不少文章与著作。从其自身经历出发,他是深信“目的证明手段正确”这种信条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也是胡适的老师)曾以《手段和目的》为题对他的观点提出商榷,进行反驳。杜威指出,“因为托洛茨基先生同样认为,‘以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一立场是唯一的选择,是某种形式上的伦理绝对主义(absolutistic ethics),是基于所谓良心、或道德意识、或某种永恒真理的判决。我希望说明:我反对所有这些教条,我的立场和托洛茨基先生的立场一样鲜明。”(《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十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网上流传着美国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关于手段与目的一段著名论述,未能找到出处,他这样说:“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如同《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的语言形象而生动。“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种桃得桃,种李得李,种子是否正确不需要树来证明,相反,树是否正确倒是由种子来决定。目的崇高必须排斥手段卑鄙,目的卑鄙手段岂能高尚?“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同样道理,通过邪恶手段达到的怎么可能是美好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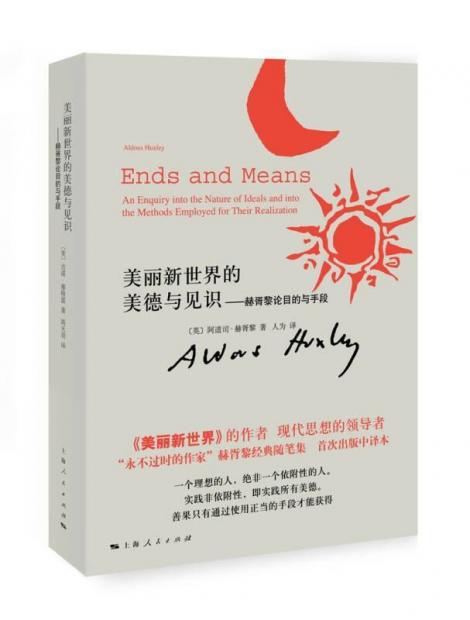
鲁迅头上曾有过“三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头衔,但他首先是文学家。文学作品的深度是由其思想深度决定的。在某方面的思想深刻(比如解剖国民性),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领域都深刻。英国作家赫胥黎,比鲁迅小十来岁,1932年他创作的《美丽新世界》,揭示了科技进步时代、极权统治下的“乌托邦”,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此时的鲁迅却撰写了多篇为苏俄“乌托邦”进行辩护与赞美的杂感与书评。赫胥黎后来在谈到乌托邦背景下的手段与目的关系时说,“善果只有通过使用正当手段才能获得。结果不能证明手段是否正当;原因很简单,正是所使用的手段,决定着所产生的结果的性质。”(《美丽新世界的美德与见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页15)的确是个悖论,柏拉图要构建一个天上的“理想国”——多么美好的目的!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呢?他强调:“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93)黑格尔为了把普鲁士国王打扮成一个至善至美、至高无上的君主——美好的目的,他的手段是什么呢?只有恩格斯这个量级的思想家才能拆穿他的把戏,“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页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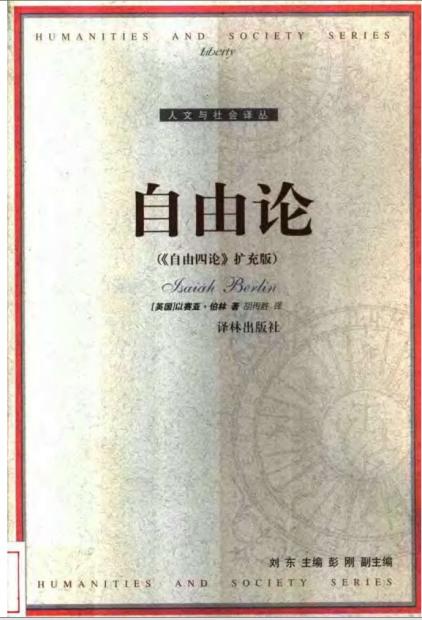
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由谁证明,也有一个证明的主体问题。鲁迅的回答很明快——由自己证明,他的原话是——“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也就是说,自己就是检验手段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没有与鲁迅接触的机会,但是他的一段言论,似乎又是专门针对鲁迅的,他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信念更有害:某些个人或群体(略)认为,只有他、她或他们惟一拥有真理,……。相信只有自己正确,这是一种可怕而危险的自大:拥有看到那惟一真理的灵眼,而如果别人不同意,错的只能是他们。”他接着指出:“这使得一个人相信对于他的民族、教会或全人类,存在着一个目标,而且是惟一一个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无论遭受多大的不幸(特别是就别人而言)都是值得的——‘造就爱的王国需要血流成河’(以及诸如此类),罗伯斯庇尔如是说。”(《自由论》,江苏出版集团,2003年,页393)
伯林的阐述并非书生之见,作为活跃于20世纪的思想家,他亲眼目睹了人类遭受的苦难。目的正确不正确,自己说了算——这一逻辑绝对不是鲁迅的发明。希特勒要打造“第三帝国”,他当然认为自己的目的是正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西斯的战车碾压了欧洲、北非的广大地区。东条英机憧憬的“大东亚共荣圈”,在他心目中这当然也是一个宏伟的目的,为了这个宏伟的目的,军国主义的铁蹄几乎蹂躏了整个亚太地区。勃列日涅夫也曾追求“发达的社会主义”,为了这个正确目的,飞船上天,核弹林立,直到其解体,人们才从其躯壳里发现他们的手段是如何卑鄙。今天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他们“圣战”的目的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手段是什么?人们已经耳闻目睹。

1925年3月,徐志摩有一次旅欧行程,他利用经停苏俄之机,在莫斯科进行了考察,虽只短短3天,他居然发现了苏俄政权的惊天秘密:“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全集》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09)这也涉及目的与手段,“升入天堂”——正确的目的,“泅过血海”——血腥的手段。苏俄政权是如何实施“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方针的,徐志摩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苏俄这个乌托邦进行了现场目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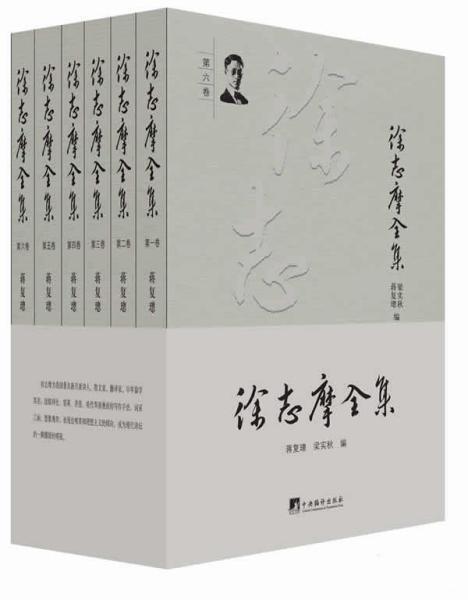
1926年7月底,胡适也曾去莫斯科考察,甚至对苏俄产生了一时的好感(不过,他到了美国很快就改变了对苏俄的看法)。作为朋友,徐志摩针对胡适对苏俄的看法,提醒其注意苏俄政治的目的与手段问题,“我们应得研究苏俄所悬的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认清了他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方法的对不对,这经程中所包含的牺牲的值得与否……”(同上书,第3卷,页144)徐志摩关于苏俄的这两段文字其实与鲁迅没有什么联系。从徐志摩后来给周作人的信中得知,徐志摩的莫斯科考察,行前是不愉快的,这种心情却与鲁迅有关系。出发前三个月也就是1924年底,徐志摩因一篇译诗和诗评,在报纸上遭到鲁迅的尖锐讽刺。除此之外,他们二人几无交涉,彼此根本都够不上论敌。文学上,他们各有千秋,思想上,互有轩轾。然而,至少在透视苏俄的本质方面,徐志摩的思想深度,不仅超越了鲁迅,也超越了胡适。
作为苏俄历史变迁的目击者,麦德韦杰夫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不维护这样的命题:似乎革命和人道主义目的可以证明,为革命而斗争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目的的人道主义决定其手段的人道主义性质,而狡诈是对斗争手段和目的的歪曲。最正确的思想,一旦用狡诈方法来维护,也不能不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徐小英《论目的和手段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相互关系》,1989年第12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这样的论述,不是什么学理,也不是什么预见,作为亲历者与过来人,流露的其实是充满沧桑的历史教训。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