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射来的冷箭
安立志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处于高不可攀的神圣地位。在一些历史教科书中,鲁迅又是一个坚持韧性战斗、从不宽恕论敌的文化斗士。鲁迅的一生。以其投枪、匕首般的笔锋作武器,不知挞伐、攻击了多少对手与论敌,其名目也丰富多彩,什么“正人君子”、“乏走狗”、“文化流氓”、“四条汉子”之类,不胜枚举,以致在建政后的几十年,竟然呈现出一个极其鲜明的文化阵线,凡是鲁迅批评过的都是敌人,凡是鲁迅赞扬过的都是朋友。如果对群星璀璨的五四文人队伍特别是鲁迅的同时代人划线的话,几乎都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这显然有悖于历史的真实。这些年来,由于更多历史典籍的出版,更多文化史料的开掘,更多研究成果的呈现,一些陈年往事,实际上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待、去分析、去判断了。
关于鲁迅与论敌的书刊,在市面上看到几种,编者都做过详尽、辛苦的汇集整理工作。总体来看,鲁迅的对手或敌人,基本都在文化领域,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其直接论战的论敌,一类是其走笔刺及的人物。这些论敌或人物,多数都是文化人或知识分子,除少数担任公职的文化官僚(比如章士钊、劭力子等人),其中基本没有军政高官,正如一些研究者注意到的,鲁迅从来不曾批评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在批评的议题上,鲁迅致力于批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以及传统文化、传统体制的某些弊端,却极少批评中国权力的劣根性,更是极少触及与当权者直接相关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些大体都是事实。这些现象的确值得分析,一种解释是,鲁迅从事的主要是文化批评,批评对象自然以文化人为主。另一解释是,鲁迅也从事社会批评,强调韧的战斗,主张“壕堑战术”,避免惹祸上身,斗争策略高明云云。

在当时,对于国民党政权,社会舆论或知识分子作为天然的监督者,仿佛有两种批评与监督方式,一种是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正面的、公开的政治批评与制度批评,矛头是向上的,其主要形式是理性的说理与驳议,如胡适、罗隆基式;一种是对国民党政权治下的某些环节进行侧面的、隐晦的文化批评或社会批评,矛头是向下(或向侧)的,主要形式是刻划或讽刺,鲁迅采取的主要是后一种方式。前者可称为“地上斗争”,后者可称为“地下斗争”。前者固然不可否定后者,后者同样不可否定前者。事实上,多年来,我们从来不提胡适等人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监督与批评,一味强调只有鲁迅的骨头才是“最硬的”。想想也是人之常情,中国历史上哪个政权会容忍民间指名道姓的批评呢?
下面要叙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我国思想与法治领域的一场人权运动。从“地上斗争”层面看,这场冲突并非发生在胡、鲁之间,但在“地下斗争”层面,他们确又相互关联。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胡适与鲁迅,作为分别留学美日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呼吁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新生活,反对旧制度,运用文字的力量,对封建文化、封建礼教、封建制度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与冲击。在这个时期,胡适与鲁迅,他们目标一致,立场协调,互相肯定,互相欣赏,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可以说,至少在当时,他们是同一战线的战友和同志。
1926年,刘和珍被北洋政府杀害,鲁迅无惧鲜血与恐怖,愤然写下了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290)1927年之后,随着北伐胜利,东北易帜,国民党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政权逐步巩固与稳定。此时的鲁迅,经常流露出对处境恶化的担忧,似乎感到了畏葸与恐惧。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鲁迅全集》第4卷,页4)其实,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仍然拥有自由办报、自由出书、自由发表、自由结社、自由成立文化机构(比如书局、学会等)的权利,只是在话语空间上比南北政府并存的北洋时期稍嫌逼仄而已。
正是在这一时期,当“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鲁迅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吞吞吐吐”之际,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则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大胆的、公开的、空前的抗争。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战略方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训政。192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下达了一道保障人权命令,其中有:“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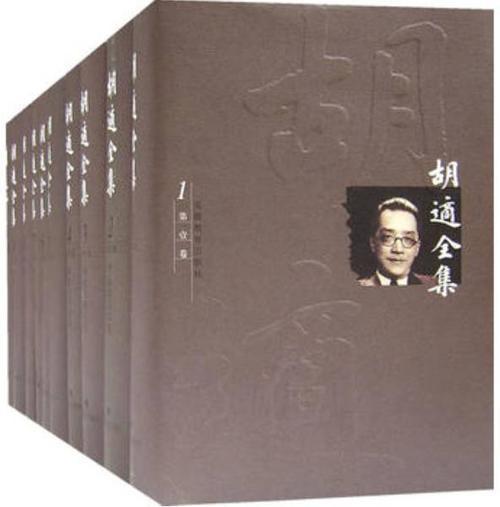
人们不曾想到,一向被贬为“风花雪月”的《新月》杂志,竟然风格大变,陆续刊出了一系列重量级的政论文章,从而揭开了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权论争。这些文章的作者以英美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其中最为活跃的有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他们对国民政府的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体现国民党政权专制性质的人权与党权问题进行了深刻而猛烈的批判。该刊率先推出的是胡适的《人权与约法》。该政令刚刚颁布半个月,胡适即对其进行了猛烈的鞭挞与抨击,胡适指出:“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这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同上书,页387)胡适矛头所向,直指刚刚实现统一、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局。面对国柄在握的国民政府,他的出击,光明磊落,义正辞严,摆的是堂堂之阵,扛的是猎猎之旗;他不屑于“痛打落水狗”,而是“挑战真老虎”。他与国民政府打得是阵地战、进攻战,而不是壕堑战、游击战,他的批评不是隐晦曲折,而是坦荡率直;他的批评不是尖酸刻薄、冷嘲热讽,而是平和理性,但却直击要害,一箭中的。而且,他对政府的批评有着扎实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既以国际学术经典为理据,又以世界人权斗争为鉴戒。200多年前,直接催生了美国诞生的托马斯·潘恩曾指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3)英国思想家穆勒陈述道,“自由指的是对政治统治者的暴虐的防范。统治者被认为必然与其所统治的人民处于相敌对的位置。”(《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胡适对于国民政府权力的监督与批评,有始有末,有根有据,正是建立在具有悠久传统的自由主义文明基础之上的。
历代帝王向以父母自居,历代官吏总以牧民为业。即使他们对国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冤狱与饥馑,他们仍然要扮演救世主。因此,国民政府的人权政令,把政府自身排除在外,似乎侵犯人权的主体只是“个人或团体”,这样的说辞体现的正是统治者共通的劣根性。由此可见,胡适所着力的是医治权力的劣根性,而不是国民的劣根性。而且,其论断与批评,具有强大的理性与逻辑力量,从而向世人揭示了政府的人权政令,不仅不符合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也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胡适对于国民党制度弊端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入木三分,这让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当局显然难以接受。
胡适的批评还不止此,为了强化文章的说服力,他竟然以国家最高领导作为反面例证,指名道姓地批评北伐起家、大权在握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他指出:“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适全集》第21卷,页389)应当指出的是,中华民国并非民主国,蒋介石则是独裁者。以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与阅历,当然认为人民监督权力是天经地义的。美国的开国领袖当初也是这么说的,“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P264)然而,那是美国的逻辑与美国的实际,却不是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的实际。大家都知道英国政治家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人们往往不知道下半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P342)蒋介石当然不是“天使”,也并不是“伟大人物”,但他当时的确拥有“绝对权力”。“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这句话有矛盾,既“总是”,却“几乎”,既有实然,又有或然。不管怎样,胡适对于蒋介石的批评,是基于理性与逻辑,合理合法,入情入理,然而,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却无异于揭逆鳞、捋虎须。这显然不是所有批评者敢于尝试的,即使“骨头最硬”的鲁迅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请看胡适的批评逻辑:“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胡适全集》第21卷,页390)胡适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公然指名道姓地批评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这在现代报刊出现之后的中国,可以说是空前的。

我们知道,国民党执政之后,曾一度实行言论审查制度。鲁迅发表的许多杂文,为了躲避官方审查,反复变换笔名,甚至许多作品是在国民政府鞭长莫及的租界和“半租界”里完成的,这从鲁迅几本以“且介亭”命名的文集,可见端倪。胡适本来“无党派”,也非“体制内”,在当时,他与鲁迅一样,也是在野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处的舆论环境都是一样的。1929年2月26日,胡适日记里保留着一份剪报,这是一位读者不失善意的规劝:“听说胡先生近来实在忍耐不住,一定要办一种什么刊物来批评党国,据我看,以胡先生的地位,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专门弄弄哲学史或文学史的好;……要知道吴淞中国公学,就在蒋总司令的势力范围,难道不怕捉将官里去而为刘君文典之续吗?”(《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358)这说明胡适对批评当局和蒋介石的潜在风险是心知肚明的。当年3月,胡适写道,“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胡适全集》第21卷,页381)胡适当然懂得直言即意味着风险,然而,他并不畏惧,并不退缩,并不隐晦,正气凛然,勇往直前。当年5月6日,胡适指名批评蒋介石的《人权与约法》义无反顾地发表了。
1927年,鲁迅被吓得“目瞪口呆”,只能“吞吞吐吐”,逃离广东,只好躲在上海滩的“且介亭”里创作杂文。早在1923年,胡适就曾公开向社会宣示:“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同上书,页316)1929年,他公然撰文指斥蒋介石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当然,胡适此文决非影射鲁迅(此时,鲁迅前述言论尚未问世)。胡适是提倡白话文的先驱,他写文章,直抒胸臆,明白畅达,他不会隐晦曲折,不会拉瓜扯蔓,在恶劣的氛围中,他从不为发表文章而变换笔名,而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公开向当局,向社会呼吁,“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同上书,页381、382)胸怀坦荡,高风亮节,本身也是战斗力。
胡适对于当局的人权批评在继续,他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不断发生侵犯人权的弊端,是因为缺乏《中华民国宪法》所致。宪法之所以不能问世,是因为孙中山借口“人民知识”、“人民程度”低下,不宜实行宪政之故。胡适指出,“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他一针见血地批评孙中山,“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同上书,页433、434)胡适冒险批评了现任最高领袖,又把矛头又直指了执政党的“先总理”。在国民党看来,孙中山是该党的“国父”与“党魂”,反对孙中山就是反党,就是“诋諆本党,肆行反动”,就这一条就可以给胡适以严厉惩治了。

在这场人权运动中,不能不提及另一位人权斗士罗隆基。他与胡适经历、气质与专业(他学的是政治学,胡适学的是哲学)迥然不同,他的文章,笔锋更为犀利,见解更为深刻,气势更为磅礴。他反训政、反党治,批判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体现了更大的杀伤力。他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中,对国民党的核心理念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引用孙中山的话指出,“党在国上”的党治思想,其实来自苏俄:“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他罗隆基批评道,“‘党在国上’、‘党权高于国权’,这当然是独裁制度,不是平民制度。”(《民国丛书第三编 中国问题》,上海书店,1932年,页34、37)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风向标。对于秦始皇式的权力,他们不会像项羽,“彼可取而代也”,推翻一个帝制建立另一个帝制;他们也不会像刘邦,“大丈夫当如是”,谄媚权力以求分得一杯羹。他们以其学养与知识,监督权力,引导社会,试图让国家变得更好,让国民少受点罪。无论在当今世界各国(包括今日中国在内)都是如此,许多知识分子批评政府的目的,并非为了颠覆政府,揭竿起义,而是促使政府运行在法治轨道上,以促进人民的自由和政府的良善。胡适等人的良苦用心,并未得到理解。
这场由自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以批判国民党的政治法律制度为发端的人权运动,引起了中国政坛的新主子——国民党当局的不安与震惊。他们开始运用所有资源予以压制。先是由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对胡适等人进行舆论攻击,称其“醉心欧化”,“目无本党”,“诋毁党义”,“不独为本党之罪人,且属媚外败类分子之显著者”。(《胡适全集》第31卷,页561)立法院长胡汉民公开指责胡适“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国家民族为牺牲”,“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页880、877)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胡适予以严重警告,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1930年2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而由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也被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査禁并烧毁。对罗隆基的处理更严重,当年4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等罪名逮捕罗隆基(一天后被释放)。后因罗隆基发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再次触怒当局,于是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免去其光华大学教授之职,从而敲掉了罗隆基的谋生之具。
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权运动之火,由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压,最终熄灭了。由于这场人权运动的批判锋芒直击国民党当局,胡适等人首先遭到的是执政当局的严厉处置与打击。然而,在这场人权运动中,他们承受的打击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腹背受敌,遭到了前后夹击。国民党当局对他们的打击是正面的、公开的。在这同时,他们也遭到背后的、隐蔽的攻击。来自正面的攻击冠冕堂皇,来后背后的攻击却阴阳怪气,而这“背后射来的冷箭”,更使他们寒心与鄙夷。

1929年底,胡适等人不惧国民党当局的文攻武吓,毅然决定将新月同仁的人权论文汇编成册,名之曰《人权论集》。胡适为之作序云:“这几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今日人人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人权问题。前三篇讨论人权与宪法。第四篇讨论我们要的是什么人权。第五六篇讨论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第七篇讨论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希望国民党的反省。第八篇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胡适全集》第4卷,页652)
这篇序言的宗旨很明确,“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同上)作为文眼,是上海滩所有的旧式文人不敢触碰、不敢涉及的,因而也是望尘莫及的。在序言中,胡适引用“鹦鹉救火”的故事,以明心志。故事是这样说的:
昔日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1929年9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保留一附件,有人给胡适写信说:“您看人家鲁迅先生便比您乖,他虽然尝说‘真的猛士,敢面惨淡的人生’,然而‘有人说我为什么不作作政治论文或者别的……无论他们(指那些以软刀谋害的)如何勾引,我却总不会上当’。(大意如此,语句是否这样记不清楚了)先前我总以为鲁迅先生这句话未免太小心了,似乎与自己的‘直面惨淡的人生’相矛盾;而今始知不然,这正是他老人家的精明处。”(《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页510)作为一种生存智慧也好,作为一种斗争策略也好,不当许褚,隐身壕堑,并非不可理解,难以理解的是鲁迅对胡适等人采取的行动。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斗争,本来就不是势均力敌。胡适等人出于信念与良知,对政府体制进行的批评与监督,虽然不是你死我活,然而,由于官方的傲慢与权力的跋扈,往往把一切批评视为寇仇与恶意。本来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控制与反动统治方面,鲁迅与胡适的所处环境与斗争目标是一致的。当胡适等人在阵地前沿,奋不顾身,猛烈冲杀之际,怎么也没想到,从他们身后袭来几阵黑枪,射来数支暗箭——鲁迅在他们背后下手了,而这才是更为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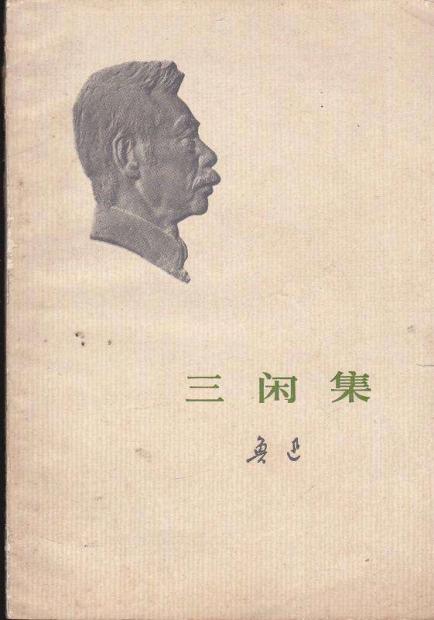
鲁迅用他那柄匕首般的刀笔尖利地嘲讽道,“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但他们不过是帮助国民党“维持治安”的“刽子手和皂隶”,“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鲁迅全集》第4卷,页163)胡适与新月同仁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批评与监督,在鲁迅笔下,竟然成了国民党“维持治安”的别一种方法。形象思维发达的鲁迅,把胡适等人遭到政府的惩罚与整治,形象地比作被贾府塞了满嘴马粪的焦大。这样的批评方式,很容易让人们想到两个成语——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鲁迅对胡适的《人权论集》进行了犀利的讽刺,“‘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鲁迅全集》第5卷,页50)真不知道这样的逻辑是如何建立的?看过胡适对于国民党政府那些大气磅礴、犀利痛快的批判,无论如何,看不出胡适等人是出于对“反动的统治”的“粉饰”。鲁迅的批评,根本不会考虑胡适的解释——“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胡适全集》第4卷,页652-653)“救火”的“鹦鹉”与“填海”的“精卫”有些类似,毕竟不是“农夫与蛇”里的“毒蛇”。无论如何,也难以得出“鹦鹉”等于“毒蛇”,“批评”等于“粉饰”的结论。难不成对于国民党的专制,蒋介石的独裁,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被吓得“目瞪口呆”,“吞吞吐吐”,只会向捍卫人权并与独裁作战的文人施放冷箭,扔臭鸡蛋,倒成了“斗士”与“英雄”?这篇名为《王道诗话》的杂文,末尾有诗为证,现将其中的名句(《鲁迅全集》第5卷,页51)摘引如下: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果然是好诗!讽刺与挖苦齐飞,褒美与贬斥一色,“博士”、“王权”、“能言”、“自夸”、“毒于蛇”、“卖廉耻”,极尽杂文之精义!很有意思,鲁迅给胡适扣了这样的桂冠——“刽子手”、“皂隶”、“奴才”。在人权运动中,胡适批评的是独裁专制,批评的是蒋氏政权,批评的是侵犯人权;鲁迅嘲讽的是批评独裁专制的批评者,抨击的是批评蒋氏政权的文化人,挖苦的是国民人权的捍卫者。批评蒋介石的人成了“皂隶”、“奴才”和“毒蛇”,这思路绝对不是杂文创作的特有思路。鲁迅的行为是不是更像在帮助蒋介石“维持治安”。有人说,此文原系瞿秋白所作,并非鲁迅所写。已经有人质疑,瞿秋白此文既以笔名发表,为何要用鲁迅的笔名?瞿秋白去世早于鲁迅,此文何以收入鲁迅文集?
三年以后,鲁迅仍然不肯放过胡适等人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比喻呢?因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鲁迅全集》第5集,页122)“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同上书,页50)追求法治、宪政的胡适、罗隆基,被鲁迅说成追求“王道、仁政”;被国民党政府警告、逮捕的胡适、罗隆基,被鲁迅说成“中国的帮忙文人”,反差为什么这样大呢?攻击讽刺遭到国民党政权打击的胡适、罗隆基,鲁迅又是为谁“帮忙”呢?鲁迅笔下提及的“王道,仁政”,这些东西与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到底存在多大差异?鲁迅大概并不想搞清楚!
毋庸置疑,胡适、罗隆基对于政府的批评与监督,其所立论的基点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英美宪政理论,他们实际上是希望按照英美的宪政体制来塑造国民政府。进入30年代的鲁迅,已经成为左翼文艺联盟的盟主,其信仰与追求不再是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他所追慕的是与英美宪政制度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苏俄式的专政制度。1932年4月,鲁迅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指出,苏俄是“工农大众的模范”,在这个模范国家,“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鲁迅全集》第4卷,页436)为此,鲁迅发表了大量杂文与译作,不仅为苏俄模式广为宣传,而且为苏俄模式强作辩护,其中的名文就是那篇他已经深受其骗的《我们不再受骗了》(同上书,页439)胡适的信念,是希望中国走上英美式的宪政之路;鲁迅的信念,则是希望中国走上苏俄式的专政之路(幸或不幸的是,鲁迅的信念在其死后得到了实现)。此时的胡适与鲁迅,他们已经不是同盟军,早已分道扬镳,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当国民党专制政权对胡适等人实行打压之际,从背后给胡适重重一击,虽然不能致其死命,至少也符合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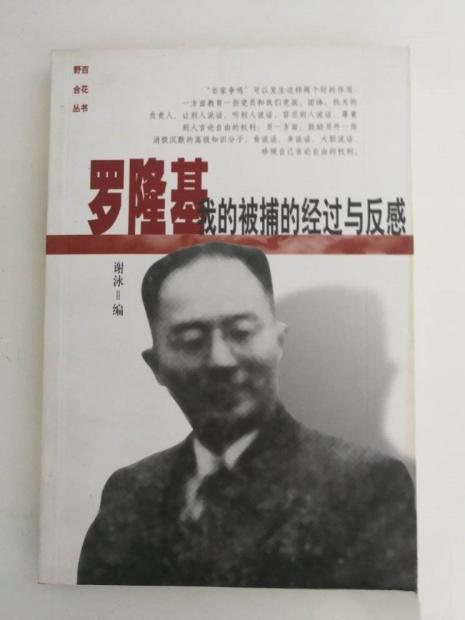
如前所述,一向“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鲁迅,从来不敢“直面”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从来不敢“直面”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因此在黑暗、恐怖的旧中国,鲁迅以其生存智慧,从来不曾坐过当局(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的监狱(倒是一位伟人设想,鲁迅如果活到1957年,却有可能坐监狱)。然而,“骨头最硬”的鲁迅,绝对敢于直面刚刚走出监狱的罗隆基。1930年3月,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结尾,鲁迅谈论的不是“翻译”,不是“文学”,而是这样一段话:“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同上书,页217)从鲁迅这些言论中,似乎能看出他对新月派遭到打压的幸灾乐祸,甚至对新月人权运动极不友善的评价,一句“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蕴涵着别样的意义。《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是罗隆基的文章,此文是为批评国民党当局对胡适的“警诫”而写的。那么,他是如何“替对方设想的”呢?罗隆基向国民政府“献策”:“本身真有好的主张及学说,对方攻不倒;对方真有好的主张和学说,我亦压迫不住。自由批评,自由讨论,绝对的言论自由,固然是危险,实际上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页87),罗隆基为胡适的被“警诫”而辩诬,而他自己则很快被逮捕,当他被释放后又是如何“替对方设想的”呢?罗隆基说:“‘人权’,在党治底下,是反动的思想。鼓吹人权,是我触犯党怒的主因。小民知罪了。这次被捕以后,……我的要求是:政府守法,党员守法,政府和党员遵守党政府已经公布的法律。”(同上书,页117)“十一月四日的拘捕,在我个人,的确不算什么。我认为这是谈人权争自由的人,应出的代价。人权自由,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这是历史上绝无的事实。……控告,拘捕,羁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这是笨人的笨法子。老子说的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同上书,页122)只因此文,可见其死不改悔,于是他在光华大学的教职被撤免,从而丢了饭碗。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鲁迅看到的罗隆基的“软”,似乎从罗隆基身上看到了一丝谭嗣同的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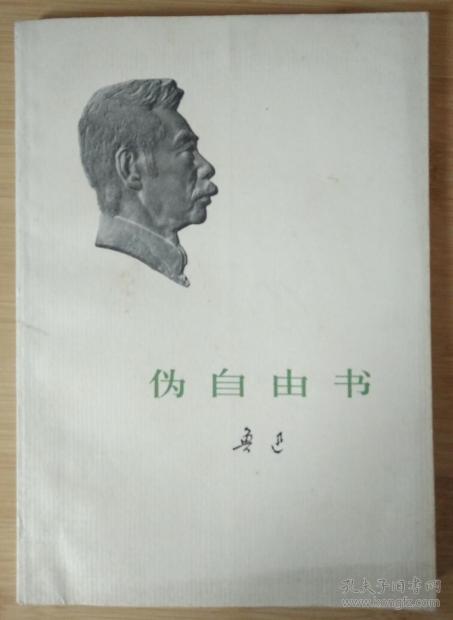
鲁迅在对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长达数年的冷嘲热讽与无情挞伐之后,写下了几句结论性的意见:“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鲁迅全集》第4卷,页217)鲁迅这话明显失实,胡适、罗隆基批评的是国民政府,批评的是蒋介石,后者显然不是“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而鲁迅对胡适、罗隆基的批评,才大体符合鲁迅自己的定义。胡适被迫辞职出洋,罗隆基锒铛入狱,大概要算“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吧,但他们并未放弃对政府的批评,但在鲁迅笔下,却成了“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生生塑造出一副小丑模样!鲁迅的笔锋的确厉害无比!
鲁迅后期的创作主要是杂文,他自己说,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诞生的(《鲁迅全集》第6卷,页3、4)。照字面理解,围剿其杂文的,有官有民,有明有暗,有软有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样的围剿面前,鲁迅是被围剿者,是受害者。然而,对于胡适的围剿就不一样了,首当其冲的是国民党官方的、公开的、强硬的、火力对接的围剿,当然也有上海滩民间的、隐蔽的、阴狠的、暗放冷箭的围剿,意外的是,鲁迅这样的“顶级杀手”也出现在这样的围剿队列中。似乎出于斗争目标的专注,胡适等人对于鲁迅的冷箭,始终未予还击;反而,梁实秋因为“硬译”陷入了与鲁迅的缠斗,却削弱人权论争的战斗力。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