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并非自由主义者
安立志

最近写了几篇有关鲁迅的文字,引来了一些留言与评论,即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是不是信奉自由主义,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活跃期,也是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期,在当时的氛围下,自由主义通常被视为健康、进步的价值体系,于是有人认为,鲁迅也是自由主义者。
说实话,我此前从未思考过这一问题。近日得暇,就鲁迅的自由观梳理了一下有关资料。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自由观”和“自由主义”,与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不是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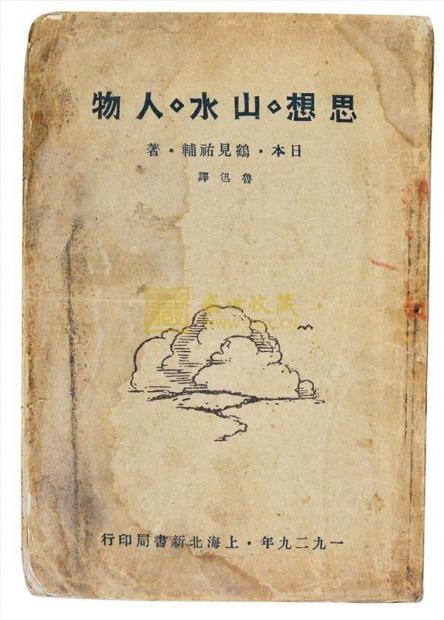
在我的印象中,鲁迅对自由主义向来不感兴趣。1928年3月,鲁迅翻译了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随笔集《思想 山水 人物》,他在“题记”中写道:“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鹤见的书中确有一篇《说自由主义》,鲁迅也专门说明,“那一篇……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299、300。以下只注《全集》卷号、页码)鲁迅翻译这位日本作家的作品,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的“美英现势和国民性”,却对作者“所提倡的”自由主义“都不了然”或“非所注意”。其实,事情远非字面这么简单。此时的鲁迅,在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上已别有所属。1925年5月30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他的头脑中,曾经“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笔者注)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全集》第11卷,页493)可见,他对自由主义兴趣缺缺,本就其来有自。
在今天,“自由”列为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贴满广场和街衢。在五四运动时,“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传入国内,学界中人,不可能回避,人们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解释。1919年5月,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一段“人心很古”的随感录,他在文中引用了一段《北史》:“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全集》第1卷,页368)
在皇权社会中,“定于一尊”的“天子”或“今上”,具有无限制的性权力,三宫六院,三千粉黛,本是“正常”待遇。隋文帝宠幸一个女子,也被后宫管着,这也太不自由了吧!这大概是“自由”这个词较为古老的中国用法。鲁迅在下面的议论中,表明了对“自由”的认识:“这又不是与现在信口主张自由和反对自由的人,对于自由所下的解释,丝毫无异么?”(同上)“主张自由”与“反对自由”的都是“信口”,鲁迅对与“自由”相关的两方显然都不重视。鲁迅的断语结合引用的史例,可以证明,他所理解的“自由”,其实就是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天马行空,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胡适比鲁迅小10岁,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之一。在鲁迅眼里,他显然也是“信口主张自由”之一人。但是,胡适作为英美自由主义的深度“感染者”,他对自由的主张,与鲁迅决非“丝毫无异”。胡适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自由主义是“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容忍与自由》,京华出版社,2006年,页155)胡适举例说,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胡适的解释是,“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因此“此瓦不自由”。(同上)中国文化的“自由”,“自”是主体,“由”是行为,自己的行为由自己做主,因此,自由也可解作“由自”。然而,在自由主义理论中,“自”当然可以理解为“个人”,不过,这里的“个人”不是指“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指“每个人”。这就有一个如何保障“每个人”自由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由,就需要有“边界”;没有“边界”,人们的行为都会乱套,人们的自由就没保障。这个共同的“边界”就是法律。波普尔的描述很形象——“流氓抗议说,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他的拳头可以挥向他喜欢的任何方向;法官聪明地答道:‘你的拳头运动的自由受到邻人鼻子位置的限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213)
鲁迅没有接受过英美的自由主义教育,又对世界上的自由主义名著缺乏兴趣,这可能是他不能准确把握自由主义真谛的基本原因。的确,“自由”这个概念,中国和外国确有不同。在许多西方学者的著述中,都明确作出澄清,自由决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直至今天,一些诋毁自由主义的人,仍然居心叵测、自设标的地把自由歪曲为十分荒谬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有”的放矢地组织批判。其实,即使在欧风东渐的清末民初,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论著,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自由的明确定义。
1748年,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强调:“政治自由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154)20世纪初,此书由严复译成中文,最初的书名为《法意》。
1762年,法国另一位思想家卢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页8)“……倘若他们企图打破束缚,那就反而会更远地离开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会把与自由相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52)
1789年8月26日,在法国大革命高潮中,制宪会议通过了《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该宣言第四条明确指出:“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人权基本文献要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1)
正是鉴于法国的启蒙进程与革命经验,1859年,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论述道:“在利害止于一身的事情上,一个人当然可以随自己的喜欢自由行动,但却不可借口别人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自由地随自己的喜好越俎代庖。”(《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25)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己之所欲,勿施于人”,应当看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升级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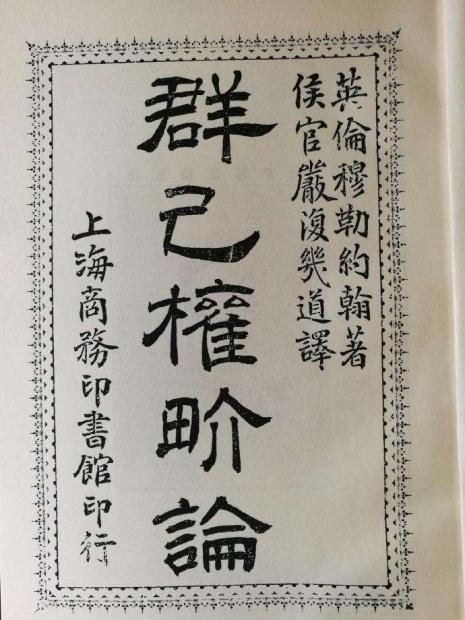
清末民初,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将其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这个书名,突出了自由的本质,即重在解决个体与群体、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应当说,这个翻译是相当准确和传神的。想不到,鲁迅在与瞿秋白讨论相关问题时说,“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全集》第4卷,页389)鲁迅对《群己权界论》的“费力”、“吃力”、“费解”,以鲁迅把握文字的水平与能力,显然与文字无关,有关的是文字背后蕴涵的精神实质。鲁迅崇尚绝对自由,反对任何限制,“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全集》第1卷,页52),这正是他不理解严复何以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的主要原因。严复深知一些国人对于自由(当时“自由”书写为“自繇”——笔者注)的误解,他在该书的“译凡例”中,极有针对性地指出,“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夫人而自繇,……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穆勒此书,即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也。”(《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Ⅶ)严复在这篇让鲁迅深感困惑的“译者序”中明确指出:“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页132)鲁迅的困惑,从根本上说,是因其未能“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至少在自由的本义上,他对自由的“权界”缺乏理解。这其实并非文字问题,而是理念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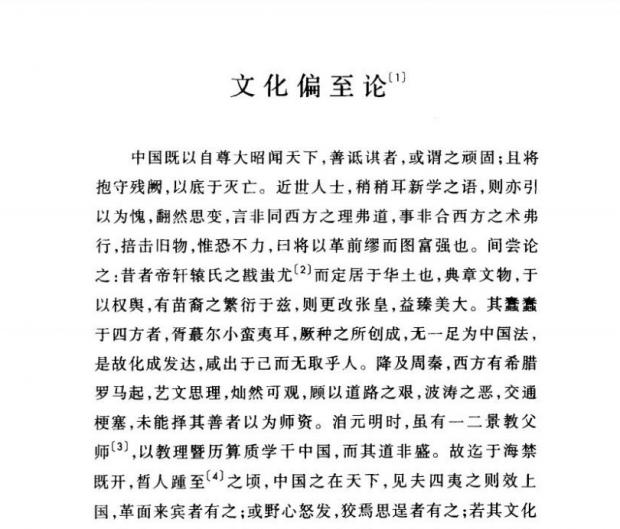
如前所述,鲁迅理解的绝对自由,并不是“每个人”的自由,而是“某些人”的自由。芸芸众生,不是“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的,享受自由是需要资格的。在他看来,只有先知先觉的天纵英才才能享有自由,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民群氓,是没有资格享有自由的。“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全集》第1卷,页52-53)鲁迅曾经主张“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人们只得先取其一”(《全集》第10卷,页300)。他当时就认为,自由的资格不是平等的,人群有“天才”与庸才之分,智者与“愚民”之别,一些“劣”“恶”之辈,甚至与“动物并等”或“不殊蛇蝎”,怎么能够平等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鲁迅才提出,要“主我扬己而尊天才”、“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这不仅与柏拉图“哲学王”的理念非常接近,也与“英雄创造历史”十分相似。由此就可理解,为什么鲁迅极少提及或拒绝倡导“民主”理念了。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是鲁迅的首创。卢梭就曾指出:“犹如牧羊人的品质高于羊群的品质,作为人民首领的人类牧人,其品质也就同样地高于人民的品质。……亚里士多德早在他们之前也曾说过,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作奴隶的,另一些人天生是来统治的。(《社会契约论》,页7)18世纪的卢梭,20世纪的鲁迅,前者推崇“牧羊人”管理“羊群”,后者主张“天才”主导“愚民”,历史在更多情况下是前后衔接的完整链条。如何提高这些“盲瞽鄙倍之众”的素质呢?鲁迅从来没有尝试过民主训练与民主实践的制度设计,他想到的是,通过那些天纵英明、永远正确的“天才”和智者的启蒙,以改造国民大众的劣根性。在这一过程中,改造的“对象”总是头脑尚未开化的愚顽庸凡之辈,改造的主体总是身膺天命、永不犯错的“天才”、智者和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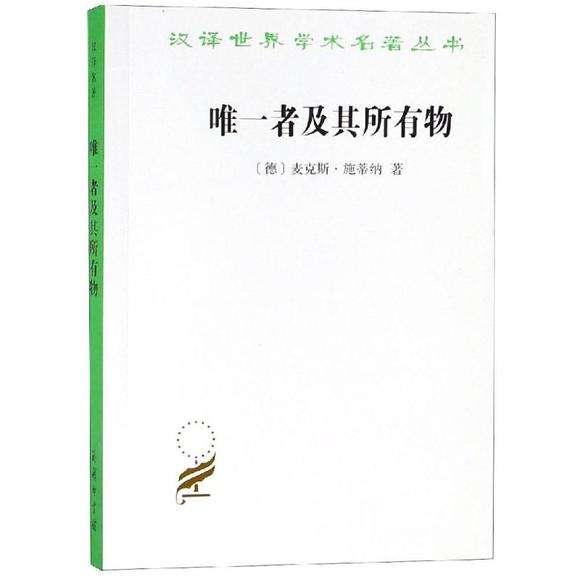
上个世纪之交,在日本求学的鲁迅,最初接触的西方潮流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较早的卢梭、穆勒,较晚的尼采、施蒂纳等人的思想流派。在鲁迅《坟》中的几篇古文里,流淌着鲜明的尼采与施蒂纳(鲁迅译为斯契纳尔——笔者注)等人的思想痕迹。作为利己主义者的施蒂纳,极力主张以我为核,随心所欲的自由,“我即是核,它应从一切包裹中解脱出来、从一切束缚着的外壳中解放而自由。如果我从非我的一切之中摆脱出来,还留下什么呢?只有我、仅仅是我。”(《唯一者与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页175)“我的权利的所有者和创造者——我,不承认除我之外的任何其他权利源泉——既不承认神、国家、自然,甚至也不承认有着他的‘永恒的人权’的人,不承认神的或人的权利。”(同上书,页221)“什么对我来说是正当的,那么它就是正当的。”(同上书,页204)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鲁迅将此概括为:“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全集》第1卷,页51)正是在这些论述里,鲁迅从张扬个性、倡导独立的角度,尽情吮吸着施蒂纳的思想元素。
恩格斯把施蒂纳称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页313),是有充分理据的。施蒂纳从根本上否定国家与法律的作用,“凡是国家即是专制政体,不管独裁者是一个或许多个,或者所有人均是主子(施蒂纳指的是三种政体,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笔者注),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互相压制,……”(《唯一者与所有物》,页211)“没有任何人能制约我的行为,没有人能给我规定我的活动,并在此给我立法。”(同上书,页210)鲁迅的观念可谓如出一辙:“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全集》第1卷,页52)鲁迅在这里表达的意思,与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别无二致,在他看来,无论是国家还是法律,无论是“寡人”(君主制),还是“众庶”(民主制),都是专制,即使是由“众意”(人民意志)构成的法律,也是对自由的限制与威胁。政府是专制,法律是专制,社区与机构当然也是专制,那么,怎么办呢?莫非人类只能“返祖”到人初状态,倒退回群居穴处、采集渔猎的森林时代。由此可见,鲁迅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全集》第11卷,页383)”上面这些议论可以清晰地看出施蒂纳对他的耳濡目染,这说明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已经感染了他的思想与灵魂。

恩格斯说,“我同施蒂纳很熟,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远非像他自己在《唯一者》一书对自己所描写的那么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页286)1845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首度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二人并不在乎恩格斯这位“好朋友”的脸面,他们运用比施蒂纳原著更长的篇幅,对施蒂纳这个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地批判与清算,文章用语也体现了两位年轻学者的辛辣与深刻。他们二人是如此评价施蒂纳这一主要著作的,“思维的肤浅、杂乱无章,不能掩饰的笨拙,无尽无休的重复,经常的自相矛盾,不成譬喻的譬喻,企图吓唬读者,用‘你’‘某物’‘某人’这些字眼来系统地剽窃别人的思想,滥用连接词(‘因为’‘所以’‘因此’‘由于’‘因而’‘但是’等等),愚昧无知,拙劣的断言,庄严的轻浮,革命的词藻和温和的思想,莫知所云的语言,妄自尊大的鄙陋作风和卖弄风骚,提升听差兰特为绝对概念,依赖黑格尔的传统和柏林的方言。总之,整个四百九十一页的一部书就好像是按照朗福德的方法所煮出来的一碗淡而无味的杂碎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页305)上述引文,只是他们二人对施蒂纳主义的形式批判,而其实质批判,篇幅太长,兹不赘引,有兴趣者可找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比阅读,好在这样的著作不难寻觅。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阐述了他们首创的唯物史观。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学说未能流传到东亚。从现有史料来分析,鲁迅没有看过马、恩对施蒂纳的批判是极其可能的。同是施蒂纳的学说,中间相隔60年,前边是马恩的深入批判,后面是鲁迅的倾力推崇,时空相隔,并不久远,二者的鉴别力与批判力,何以如此悬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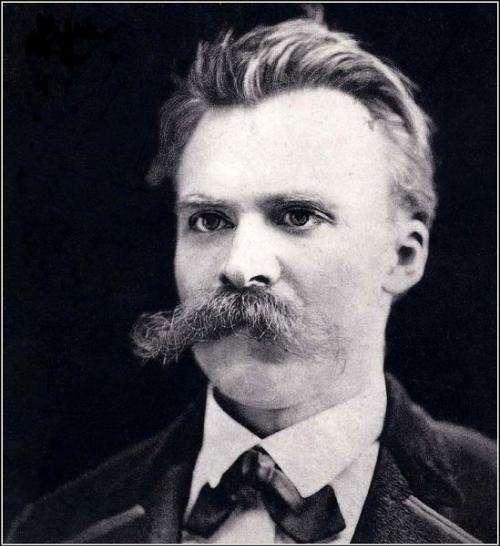
有人说,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少他年轻时不是。他在年轻时即已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鲁迅早年在日本求学,首先接受和推崇的是尼采哲学。尼采哲学有两对基本范畴,一是“超人”与“末人”,一是“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字里行间,尼采都在肯定前者,强化前者,鄙视后者,否定后者。尼采指出,“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根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9)尼采自己规划了生物进化的链条,即猿猴—人类—超人。超人当然优于人类,而人类只对猿猴具有优越感。夹在猿猴与超人中间的人类不光是“过渡者”,也是“没落者”,尼采将之称为“末人”。所以,尼采的进化序列其实是:猿猴—末人——超人。尼采说,“超人的对立面是末人:我在创造了前者的同时也创造了后者。”尼采的“超人”与“末人”是一组对应、相关的范畴。但在国人的笔下或口中,却往往把它理解为本国传统的“大人”与“小人”。当然,在尼采那里,“末人”并不是正面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尼采不知从何处得来的印象,居然把中国人视为“末人”,他在未完成的遗稿中有这样的文字:“末人:一种类型的中国人”。他指出:“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大人物的知足,导致求变的能力已经灭绝达数个世纪。”(《尼采注疏集:快乐的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03);他又写道:“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正义和和睦的王国是值得向往的(因为无论如何,那会是一个极其深度中庸化和中国人式的国度)。”(2019年10月29日《哲学研究》,孙周兴文)其实,对于中国如此评价,尼采并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负面的一个,马克思也曾将中国说成“这块活的化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页545),甚至贬为“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同上书第9卷,页111),认为中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同上书第12卷,页587)尼采所说的“末人”,当然不包括鲁迅这样的身负启蒙、教化使命的智者,而鲁迅小说中的形象却几乎都是“末人”。鲁迅作为五四运动前后致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者、教育者,扮演的显然是“超人”角色。鲁迅在翻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序言》的“译者附记”中曾有两句概括,“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全集》第10卷,页483)他在另一处说,“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全集》第5卷,页295)对于尼采“超人”与“末人”的定义,鲁迅已经融会贯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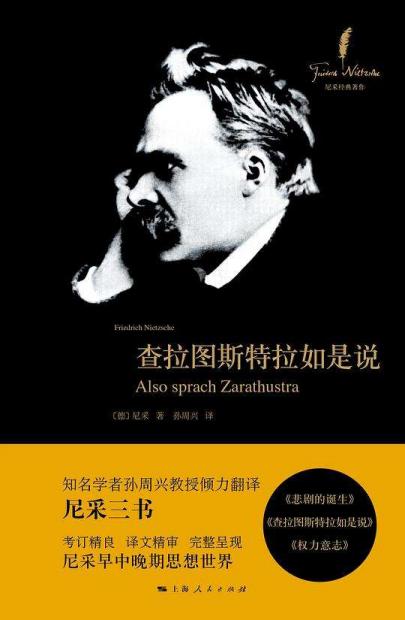
鲁迅大声呼唤聪明盖世,特立独行的尼采式“超人”,“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隲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全集》第8卷,页27)鲁迅本来是清楚的,“不和众嚣,独具我见”,固然很像思想界的灯塔,但这也是独裁者的特征。鲁迅推崇尼采,“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全集》第1卷,页53),是因为他接受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与唯意志论,从内心深处体现出追慕与崇拜。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其张扬个人价值,否定群体价值的极力强调,“故民中之有独夫,昉于今日,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全集》第8卷,页28)他怀念古代的“以独制众”,反感今天的“以众虐独”,认为这些都是“灭裂个性”。
1907年,他饱蘸深情地说:“德人尼佉(Fr.Nietzsche)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全集》第1卷,页50)失望于当代,寄望于来叶,于是,他把尼采的哲学高高举起,称之为“新思想之朕兆”,“新生活之先驱”(同上书,页51),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
鲁迅追慕尼采的“超人”说,却对“众数”(人民群众)没有任何信心,甚至相当蔑视。他是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在他眼里的“众数”,大抵阿Q、华老栓、祥林嫂之类。因此,在其早期文章中,他反对立宪、国会;在其后期文章中,从未提及民主、民治。他不仅从未主张过人民当家做主,反而主张,“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同上书,页53)这说明,他坚信以少数统治多数,以“天才”统治“庸众”,以“超人”统治“末人”,甚至“以一人治天下”,大约是他心目中最为理想的管理方式。在这种管理体系之下,甚至不惜把“多数”、“庸众”、“末人”作为“牺牲”,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
鲁迅坚信,他这样论述是有道理的。鉴于“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同上书,页52)面对这些以“顽愚”、“伧俗”和“伪诈”为特征的“凡庸”或“众数”,“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同上书,页53)“是非”和“政事”没必要向民众公布,对于这些浑浑噩噩的群氓,只能贯彻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成为民主政治的主体,明辨是非尚且做不到,何况治国理政!由此可见,鲁迅也曾对改造国民性信心不足。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超人”下凡,“圣人”出世。于是,他急切地呼吁,“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出不了“超人”,“英哲”也凑合。“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同上书,页53)社会只能以“超人”引导“愚民”,以“英哲”启迪“凡庸”。“超人”前面引导,“愚民”后面随从,此即所谓“一导众从”矣!正因如此,如何解决鲁迅提出的这一世纪难题——“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换句话说,是要“英哲”还是要“凡庸”?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单项选择,鲁迅随即给出了标准答案——“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同上书,页54)也就是说,“英哲”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对“英哲”是“希冀”;“众人”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对“众人”可“舍弃”。
有人指出,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立人”。鲁迅两句格言,“任个人而排众数”,“人立而后凡事举”,都是出自这篇文章。然而,许多人并未注意到,鲁迅的“立人”,并非“立”“所有人”,也并非“立”“每个人”,从鲁迅反复提及的“排众数”与“置众人”中,人们看到的是,他要“立”的其实只是“英哲”与“超人”,而“英哲”与“超人”之外的“众数”或“愚民”,是随时可以“弃置”和“牺牲”的。由此可见,先不论这种思路是否符合鲁迅反封建的初衷,至少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即就改造国民性而言,在鲁迅的心目中,也并不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是依靠鲁迅这样的“超人”或“英哲”,对广大愚民进行启蒙、把脉或诊治。
1754年,卢梭曾这样指出:“关于自由这一问题,正如富有营养的固体食物或醇酒一样,对那些习惯于这种饮食的体质强壮的人固然大有补益;但是对于生理上不宜于这种饮食的身体软弱的人,则极不相宜,终于会败坏他们的健康或使他们沉醉。……倘若他们企图打破束缚,那就反而会更远地离开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会把与自由相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52)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欧风美雨,涤荡华夏。外来的思潮与文化,并不都是甘霖喜雨。在这些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们迷了心智,乱了方寸,不仅未能“洋为中用”,反而成了“洋人”的俘虏。一些五四人物后来迷于苏俄模式,就是历史的误读。不知鲁迅当年是否也有同样的担忧?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