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笔下的民族主义
安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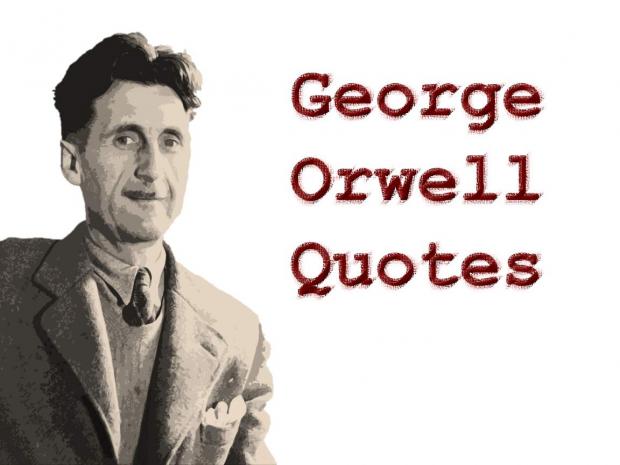
说民族主义,首先要说民族;说民族,首先要说中华民族。曾经听到两个故事,都与“中华民族”有关。前年暑假去湖南采风,在去张家界的旅游车上,导游小姐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华民族通常自称“炎黄子孙”,但湘西苗族却不认可,他们自称是蚩尤子孙。另一则故事见于近年的报纸。有人撰文称,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岳飞与金兀朮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宋金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内部战争。这其实是以今天的国家和民族现状,去框定800多年前的历史。
由中华民族谈到民族,由此导出的种种观点,逐步向民族主义靠拢。据美国学者路易斯·斯奈德研究统计,近代以来,至少存在200 种以上不同含义的民族主义(凤凰资讯:《民族主义解释》)。因此,在一篇文章中,很难说清民族主义这样复杂的问题。
现实如此复杂,只好纸上谈兵。在这里,只是介绍一下奥威尔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札记》(《政治与文学》,乔治·奥威尔著,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本书引文以下只注页码)。奥威尔这个外国人,读者可能陌生,但要提起《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的作者,可谓如雷贯耳。作为英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一生反对极权主义的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奥威尔短暂的一生(只活了47岁),在世界文学界获得了广泛赞誉。《关于民族主义的札记》只是一篇不长的社会评论,这篇写于1945年的文章,分析的是英国社会的民族主义问题。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鉴于民族主义问题过于复杂,奥威尔首先对概念进行了界定,他指出,“我所谓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指一种习惯,它假定人类可以像昆虫那样加以分类,数百万人或者数千万人可以集体被贴上‘好的’或‘坏的’标签。其次,我指的是将自己等同于某个单一的民族,认为该民族是不受道德评判的,并且以推进该民族的利益为唯一义务的习惯,……”(P282)由此可见,民族主义首先被奥威尔视为一种习惯,而且是一种负面的习惯。
在我国的网络空间里,充斥着一些爱国主义的喧嚣,这些人往往被另外一些网民冠以“爱国贼”、“愤青”、“自干五”之类的称呼。这些群体的声音到底如何归类,应当归为“爱国主义”,还是应当归为“民族主义”?奥威尔特别指出,“切不可将‘民族主义’混同于‘爱国主义’。”(P283)奥威尔的年代没有互联网,当然不存在网上舆论,但思想、主义、观念、意识这类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东西,并不是机械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方式在时空上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威尔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分,仍然具有认识价值。奥威尔不是马克思,他的看法是针对英国社会而言的,当然不能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笔者介绍奥威尔的观点,提供的只是一块他山之石。
如何区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奥威尔指出,“我所说的‘爱国主义’是指献身于自己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某个地方或者某种生活方式,但并不想通过暴力手段强加于其他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文化上,爱国主义的本质都是防御性的。”(P283)奥威尔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暴力手段”与“防御性”的问题,在下面的论述中,它将被作为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标志之一。“而民族主义则是与权力欲密不可分的。每个民族主义者的最高目标,是确保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声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他所选择的、甘心将自我沉没于其中的那个民族或者团体。”(P283)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艾利娜·辛肯恩则指出,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把自己作为一国公民的自豪感,单纯建立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之上。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优秀,并因此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国家。所谓“爱国主义”,则指人们认为自己与祖国之间存在情感上的密切联系,而这种具有自豪感的联系,往往不涉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主要生发于对本国特质的欣赏。(2013年12月18日《青年参考》A03版)奥威尔与辛肯恩分别定义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概念上具有一致性。
在这里,我们不必区分爱国主义中的“国家”与民族主义中的“民族”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思想观念,仅从奥威尔的表述中,也可感受到其中的差异。爱国主义体现出和平、开放、理性的特点,而民族主义往往体现出暴力、封闭、非理性的特点。奥威尔也指出,英国当时的“民族主义是由自欺为基础的权力欲。每个民族主义者有可能既极端不诚实,同时又毫不动摇地坚信自己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因为他确信是在为某个比自己大的团体服务。”(P284)“他所想的总是胜利、失败、大捷或者屈辱。他认为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就是大国的兴衰史,在他看来,历史上发生的每个事件,似乎都证明了他所属的团体正在兴盛,而其敌人正在衰亡。”他们盲目而偏执地坚信,“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似乎世界上光明的前途永远烛照和青睐他们这个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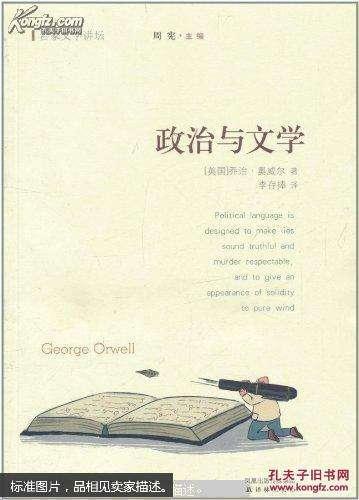
二、民族主义的特点
可能与奥威尔身为小说家的经历有关,他的笔法白描、平直、客观、恬淡,虽然是政论文章,聊聊数笔即已勾勒出民族主义的清晰形象。他把民族主义的特点概括为着迷、不稳定、不顾事实三个方面,他的看法没有强烈的褒贬色彩,却具有穿透社会与人心的逻辑力量。
我对奥威尔概括的三个特点,作如下理解:
一是盲目性。民族主义指向的主体通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政体。民族主义者对之痴迷、溢美与维护,往往是盲目的。“文革”前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曾要求,“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2010年《同舟共进》第12期),那是自上而下的要求;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对民族、团体、政体的迷信与盲从,是自下而上的情感。正如奥威尔所说:“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除了论证他所属团体的优越性以外,几乎都不想、不说、不写别的。所有的民族主义者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掩饰自己的忠诚。对他所属团体的一点点诋毁,或者对敌对组织的丝毫赞扬,都会使他义愤填膺,必得进行严厉的回击,方能平息。”(P287)他不无讽刺地指出,“如果他选定的是一个国家,……该国家不仅在军力和政治美德上占优势,而且在艺术、文学、体育、语言结构、国民体型的优美程度甚至气候、风景和厨艺上也占优势。”(P288)用民间语言来表达,看别人是“豆腐渣”,看自己是“一朵花”。自己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却能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幸福的生活像天堂”,想当然地认为他国人民整天“水深火热”、“流离失所”;他们整天被代表,总是匍匐在地上,却自己感到已经站起来了,一直当家作主,而且确信这种现状是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原本就是奴隶,却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604),从而歌颂之、赞美之,以“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不过,“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同上)鲁迅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概括道:“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全集》第一卷,P334)
二是选择性。奥威尔指出:“在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中,有些事实既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既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一个已知的事实是如此无法容忍,因此民族主义者会习惯性地将它撇在一边,不让它进入自己的思维过程,或者它可以进入所有的考虑之中,却从不被承认它是个事实。”(P291)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选择。不能说民族主义者没有价值观,民族主义者也标榜真善美、公平与正义。然而,民族主义一旦进入人的精神世界,真善美、公平与正义全部扭曲变形,因为他们“评判行为的好与坏,不是根据行为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看行为人是谁。”(P290)如果某一好事是“我们的人干的”,那么,一定会大赞特赞其如何真善美、公平与正义,即使够不上档次与水平,与这些伟大价值观根本沾不上边,也要极力往上攀,甚至创造出超迈真善美、公平与正义的光辉形象,不惜添油加醋,连篇累牍,渲染不已。如果这一事件是“他们的人干的”,无论这些事物如何货真价实地体现出真善美、公平与正义,他也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鸡蛋里头挑骨头,指责其“不完美”、“有缺陷”,非要将好事辩证成为坏事不可;“几乎所有的暴行——虐待、劫持人质、强迫劳动、集体驱逐、不经审判而监禁、伪造、轰炸平民——假若是‘我们的人’干的,就都可以改变其道德性质。”(P290)无论多么邪恶、丑陋与无耻,只要是“自己人干的”,他们都会置若罔闻,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正如奥威尔所说,“民族主义者不光对自己一方干的坏事不予谴责,而且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本领:对这些坏事充耳不闻。”(P291)如果是“他们的人干的”,则另是一张嘴脸,就会紧紧抓住这一把柄,又是跨洋连线,又是现场直播,铺天盖地,喋喋不休,上纲上线,夸大其辞,甚至无中生有,口诛笔伐,不把对方搞臭、搞垮决不罢休。对于我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些人对俄、日两国的态度更能说明这种选择性。近代以来,俄国(无论是沙皇还是苏联)与日本,是对中华民族造成灾难最为惨重的两个民族和国家。前者鲸吞了我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屠杀了我国成千上万的同胞(比如江东六十四屯),不仅这些领土至今未被归还,而且从未表达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同样有意思的是,我国也从来不要求对方道歉。由于其极权主义的政权性质没有改变,即使在当代,仍然给我国造成重大威胁与损害(比如1969年珍宝岛边境冲突之后对我国的核威胁)。特别是近年来,为了加强对我国的战略遏制,蓄意武装我国的“潜在对手”如印度与越南,向其兜售先进武器,为其提供战略支持。去年以来,因公然侵占邻国领土(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而受到国际社会制裁。日本近代以来侵占了我国的台湾与东北三省,其铁蹄曾经蹂躏了半个中国,甚至在攻占南京之后屠杀了我国同胞30万。然而,“二战”结束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侵占我国的领土被迫吐出,日本军国主义被盟国改造成为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国家,其发动战争的机制与能力受到了严厉的剥夺与控制。然而,我国一些人,面对这样两个民族与国家,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立场与态度。特别是近年来,国人经常不断地敲打日本歪曲历史,批评日本扩军备战(当然是必要的),反而对俄国的侵略扩张行径置若罔闻,不置一词,甚至在其侵略克里米亚之后,却曲为之辩,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不敢向其当面提出。由此可见,奥威尔批评一些民族主义者,“对相似的事实之间的相似点视而不见,是所有民族主义者都具备的本事。”(P290)可谓一针见血。
三是可变性。奥威尔指出:“民族主义感情虽然强烈,但并不妨碍民族主义者转换门庭。……民族主义者可以并且经常钟情于某个外国。你会发现,伟大的民族主义领袖,或者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甚至不属于他们所美化的那个国家。”(P288)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民族主义者最典型的表现,集中体现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初,实行了对苏一边倒的政策。这远不是中国人钟情苏联的全部原因,其实,我们的执政党本身就是在苏联的扶持下诞生的,也就是说,我国执政党的血脉里流淌着苏俄的基因。因此,新政权建立初期的10余年,中苏之间维持着一种名义上的“同志加兄弟”、实质上的“小兄弟与老大哥”的非正常国家关系。奥威尔指出,“崇拜多年的某个国家或者团体,可能突然变得令人厌恶,于是就立刻移情于另外一个对象。”(P289)的确好景不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两党两国交恶,双方先是嘴巴官司,文字攻击,继之口诛笔伐变成了枪林弹雨、大炮坦克,接着大动干戈、大打出手,在我国的东北、西北边境,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与流血事件,甚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对我百万大军压境,并准备对我实施核打击,全中国被迫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整个中华大地到处在“深挖洞,广积粮”,以防苏军的全面侵华。此时的苏联,已不是先前的“同志加兄弟”,而是随时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苏修”、“新沙皇”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国,开始时“九评”苏共的反修文章连篇累牍,继之谴责沙俄侵华的纪录片不断播放。此时的中国人,全都处于苏军坦克袭击与核武器威胁的阴影之下。要知道,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上双雄并峙的超级大国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在网络上涌现大批的“黄俄”(亲俄的中国人)。正是在举国上下笼罩在战争阴云的恐怖氛围中,中共领导人作出了中美建交的战略决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为这一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邓小平,这一决策并非仅仅为了对抗苏联的侵略,从根本上讲,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格局中正式启动的。奥威尔指出:“每个民族主义者都受到一种信念的困扰,即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他将自己的部分时间花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想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P292)时移势易,这个战略不知从何时发生了逆转,尽管改变的原因非常复杂,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之后,一些人似乎又开始移情别恋俄罗斯,重新走上了联合俄国、对抗美国的“冷战”时期的老路,尽管中俄形式上并未结盟,但从世界舆论、国际影响以及外交效应来看,中国已经被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之上。当代国际政治毕竟不同于纵横捭阖、朝秦暮楚的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政治毕竟有着基本的人类正义与国家道义。在国际关系之间坚持正义、主持公道,至少是大国责任的具体体现。对于这样一个“二战”前与德国纳粹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战后仍然穷兵黩武、侵略扩张,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的政权,我们不仅对之进行外交支持,而且对其经济输血和战略援助。由此可见,考察中国从亲苏到反苏再到亲俄这个漫长的移情、易变的过程,可以更加明确地感受到奥威尔论断的正确性——“民族主义者唯一保持不变的,是他的心理状态:他热爱的对象不仅可变,而且还可以是假想的。”(P289)“移情后的民族主义,就跟替罪羊的作用一样,是一个不用改变自己的行为就能达到解脱的好方法。”(P289)
四是暴力性。奥威尔指出:“虽然民族主义者没完没了地思索权力、胜利、失败和复仇,但他对客观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常常并不太在意。他所想要的,只是他所属的团体能够压倒其他的团体,因此,丑化其对手要比仔细地考察事实、以确定事实是否支持他的论断,能更容易地达到他的目的。”(P293)如前所述,“民族主义”区别于“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其暴力性。由于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方式缺乏理性与逻辑,在表现形式上,与我国盛行的极“左”思维庶几近之,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充斥着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二元对立。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世界里,不同看法与观点的人群,无法进行理性、平和、冷静、客观的对话与沟通,而是随时爆发出戾气与暴力。首先是语言暴力。这一特征在网络世界尤为突出。一些有着民族主义思维方式的网民,他们在网络上的存在方式,大多是以跟帖呈现的。对于他人篇幅较长的网文,他们甚至缺乏通读一遍的耐心,根本不屑于了解其立场与思想,浮光掠影看过几行,感觉味道不对,立刻恶语相向,谩骂攻击。这些人似乎不会运用正常人的语言与他人交流、探讨问题,而且缺乏与之讨论、切磋的水平与能力,他们留下的跟帖,往往满屏污言秽语,肆无忌惮地糟蹋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跟帖者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一言不合,恶语相向,每年网络上都会制造出以谩骂为特征的最新污染词汇。在一些论坛,此种网民成群结队,邪恶横行,腥臭遍地,致使整个论坛变成了猪圈与粪堆。我国的互联网生态,既是舆论生态,也是社会生态,厕身其中的人们,无论在现实世界扮演何种社会角色,他可能是家庭中的孝顺子女,也可能是单位里的优秀员工,一旦隐身于网络上的马甲,人性深处的阴暗与邪恶,立刻暴露无遗。因此,从根本上讲,网络世界也可以称作人性生态。这一生态不仅体现了民族主义的大肆泛滥,更加体现了极其失败的思想文化建设。更为可怕的是,其中的一些人竟然是官方培训与招募的网络水军。二是行为暴力。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思潮,原本不应酿成社会暴力。由于这种思潮本身非理性、非逻辑的性质,也就难免出现一些不雅、不智、不法的行为。在网络世界,语言暴力危害的只是网络舆论与网络氛围,一旦进入现实生活,民族主义就会酿成社会冲突,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近些年来,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发生之后,我国官方似乎并未吸取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最终导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历史教训,仍然将民族主义当作可以借用的民心、力量与工具。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但却通过具体法律对这些权利进行了严格限制。比如,公民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要求政府履行法律义务的游行示威,从未见过政府批准的先例,相反,一些体现了浓厚民族主义情绪的游行示威,公然在各大城市举行。从现场警察力量的保驾护航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游行示威带有鲜明的官方鼓励、怂恿、默许、支持的特征。近年来,这类游行示威影响最大的有三次,一次是抗议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次是抗议在法国发生的藏独分子抢夺北京奥运火炬,一次是抗议日本将我钓鱼岛国有化。然而,由民族主义这种缺乏理性的社会思潮所支配和笼罩的广场与街道行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暴力,比如美国驻华大使馆与成都领事馆遭到破坏与冲击,法国连锁商业企业“家乐福”受到冲击与恐吓,特别是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砸毁日系轿车,甚至打伤无辜民众的事件,甚至北京某大学的教授韩德强竟然对观点不同的一位老人施之以暴力。这些事件都充分证明了这一问题。这种不能“帮忙”、反而“添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暴力行为,不仅给外交部门带来外交被动,而且严重损害了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国际形象。
三、民族主义的惯伎
民族主义者非理性、非逻辑,在宣扬其观点、实施其行为的过程中,自然不会顾忌其看法、其行为是否符合理性与逻辑。其中常见的行为方式至少有以下三种。
其一是罔顾事实。奥威尔指出,“假如你头脑中的某个地方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忠诚或者仇恨,那么某些事实即便明知是真的,你也不会承认,……”(P300)“如果是‘我们的人’干的事,天大的罪行也可以宽恕,哪怕在心底里认为那是不公正的。即使不否认发生了犯罪行为,即使心里很清楚那种犯罪跟自己在其他案件中谴责过的行为一模一样,即使承认它是不公正的——你还是不会感觉到它是错的。只要牵涉到忠诚,怜悯就会失效。”(P301)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相?在民族主义者眼里,为我所需的就是事实,就是真相。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不惜移花接木、削足适履、偷天换日、弄假成真。民族主义者似乎佩戴了一副特异眼镜,两只镜片功能不同,一片专门观察自己欣赏的民族、团体与国家,一片专门观察自己讨厌的民族、团体与国家,即以我国媒体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为例,CCTV的“新闻联播”可以算作一个典型范例。这是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典范。30分钟的新闻结构,被网民解构为:前面10分钟——“领导很忙”,反映的不外是中央领导人的冠盖往来,视察调研,开会讲话;中间15分钟——“中国很好”,反映的都是市场繁荣、科技进步、人民幸福、社会稳定;最后5分钟——“外国很乱”,报道的都是外国的地震飓风、枪战爆炸、瘟疫战乱等等。在国际新闻方面,央视对美国的连线报道是最多的,不是种族歧视,就是校园枪击,从未报道过美国的民主法治与公民自治,总之都是坏消息。奇怪的是,美国从未对央视蓄意否定美国的大好形势提出过强烈抗议?媒体对日本的报道也不少,不是参拜神社,就是扣我渔船,极少提到日本的社会治理与国民素质。我国媒体对朝鲜的报道更是谨慎选择,从未提及其逆流而上的三代世袭,更不提动用高射炮消灭政敌的伟大创举。我国媒体对俄罗斯的报道则从来没有坏消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出兵乌克兰,却主动寻找角度为之辩护;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经济凋敝,仍然报道其人民如何同仇敌忾,而普京本人在我国媒体上几乎成了一个坚定反美,抗拒制裁的国际英雄。
其二是罔顾历史。奥威尔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宣传性作品,几乎可以说都是造假。客观事实遭到压制,日期被更改,引文被剥离开上下文,并且被设法改变了原来的含义。如果某件事被认为不该发生,就不会被提及,最终会被否认。……当然,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影响当代的舆论,而重写历史的人可能真的以为自己是在将事实插入过去。……更有可能的是,他们觉得自己对历史的叙述正是在上帝看来确曾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受益匪浅重新编排历史记载的做法就是正当的。”(P292)奥威尔说的是70年前的英国,他的分析在今天仍有意义。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观的确如此,自己拥戴的民族与政体,只能历史辉煌,只能根正苗红,历史上有罪恶也被说成无罪恶,即使歪曲篡改历史,即使隐瞒抹杀历史,都是正当的,比如沙俄和苏联对我国的侵略与欺凌,谁要提及这些问题,美其名曰,不要“翻历史旧账”,不要“纠缠历史细节”。而对自己反对的民族与政体,则是紧紧揪住历史问题不放,无时无刻地在翻着历史旧账,每日每时地在纠缠历史问题,比如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问题,总是理直气壮,总是义正辞严,必须“以史为鉴”,必须“正视历史”。如果对方也用这样口径要求中国如此对待自己、如此对待俄国,岂不成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而在俄罗斯与日本的对比上,这两个历史上罪行累累的侵略者,在“二战”结束以后,其国家性质、外交政策、国际声誉是如此不同。俄罗斯历史上侵略、今天仍在侵略,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却不置一词;日本历史上侵略,战后受到国际社会剥夺、改造与遏制,其国体、政体已经失去发动侵略战争的机制与能力。在一些人眼里,今天的日本仍然是与70年前一脉相承、毫无变化的日本军国主义,仍然亡我之心不死。历史是一个过程,不仅要观察全部的历史过程,而且要考察历史在现实中的延伸。
其三是价值偏爱。奥威尔分析了当时英国内部存在的三种民族主义倾向,即积极的民族主义、转移的民族主义、消极的民族主义。转移的民族主义有五种表现,其中之一即和平主义。从奥威尔的分析可以看出,英国的这种和平主义与我国的民族主义有些相似。奥威尔指出,这些和平主义者,“他们真实的动机似乎是对西方民主制的仇视以及对极权制度的向往,尽管他们没有明说。……他们并不是不偏不倚地两方都骂,而是专门骂英国和美国。此外,他们一般也不谴责暴力本身,而只谴责西方用以自卫的暴力。”(P296)这让我们想起我国近年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从来不曾谴责萨达姆、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如何残害民众,如何内部倾轧,如何侵犯人权,如何威胁邻国,如何发动侵略,却对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如何误伤平民,如何炸死妇女儿童,如何留下一个烂摊子,大做文章。民族主义者由于其偏执的价值偏爱,狭隘的是非观念,从来不曾具有一贯的、统一的价值标准与是非界限。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