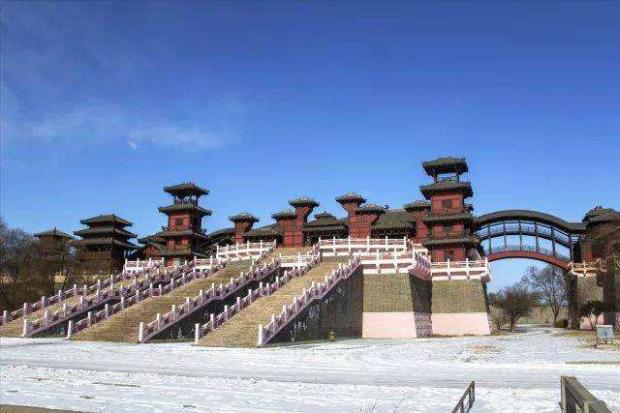
三千余年,二十五史,连绵不曾中断,自豪者谓“雄汉盛唐”,激进者曰“脏唐臭汉”。掌灯展卷,历历在目者,无非宫廷内争,沙场外战,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倾轧史、相斫史。“人民创造历史”,“朝廷书写历史”,除了赋敛与徭役,青史似乎真的没有百姓什么事儿。
即使从黄巾起事算起,三国也不到百年。天下三分,鼎足而立,人们评话纵横捭阖,波澜壮阔,人们演义金戈铁马,运筹帷幄,人们看不到,兵荒马乱,千里白骨,饿殍遍野,生民涂炭。三国争雄,面对东吴、西蜀,曹操是当然的主角。他既是征讨者,也是统治者,他对军阀混战感同身受,他对民不聊生历历在目。他经历了“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也目睹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这一点上,曹操的良知与悲悯并未丧失殆尽。正因如此,这首《蒿里行》才有了诗史的味道。

元人张养浩词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历史不分年代,黎民百姓的非正常死亡,无非来自天灾人祸,最常见的是战争、天灾和瘟疫。从汉末到魏初,天灾并不显著,然而却兵连祸结,瘟疫蔓延。赤壁之战,瘟疫正在肆虐。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领80万大军“旌麾南指”,“会猎于吴”,“赤壁之战”失败了,主要败于周瑜的火攻,与孔明“借东风”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还有另外的因素,曹操一方说,“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刘备一方说,“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三国志》,中华书局,1971年,页31、871)阮瑀说:“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462)这显然在为失败辩护,但并非毫无道理。这说明曹操的赤壁败绩,并非仅仅因为人谋不臧,“敌人”还有援军,那就是瘟疫。

东汉末年这场瘟疫持续了多年,对社稷民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是同时代人,亲历目击了这场大疫,他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页20)他以医者的眼光认为,这场瘟疫实为伤寒而起。瘟疫的结局是悲惨的,张氏二百余口的家族,竟然死去三分之二。
梁方仲先生研究汉末三国的人口,考察了大量古代文献,结论是惊人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人口约为5648万;三国时魏蜀吴三国总人口仅约773万。(《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页28、56)相距不过六七十年,后者不到前者的十三分之一,将近五分之四的人口消失了。梁方仲先生的考察是宏观的,而张仲景家族的遭遇则从微观层面提供了证据。按照上述分析,汉末三国人口的急剧下降是非正常的,主要因素就是战争与瘟疫。
然而,这种涉及千百万普通民众生存、生命状态的重大事件,在古代史籍中极少反映,似乎史家只关心军国大计,宫廷内幕,战场输赢。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这场大瘟疫,《献帝纪》只记下了“是岁大疫”四个字,即使在“五行志·疫”的专项史料中,也只写下两个字——“大疫”。(《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页389、3351)《三国志》中“大疫”二字,更是只关注之于军事行动的影响。

政客与史官不同,他们关心的是社会情绪与政权稳固。曹操作为主政者,面对疫情,并非无所作为。他先后下达《存恤令》和《给贷令》,针对的都是战“疫”行为。虽是政府公文,仍然充满温度,甚至下达了赈济、抚恤标准。建安十四年的《存恤令》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建安二十三年的《给贷令》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三曹集》,岳麓书社,1992年,页17)政客其实是不希望在“负能量”上留下纪录的。对于三国时期这场瘟疫的纪录,其实是由作家和文人完成的。

首先是陈思王曹植的《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三曹集》,页307)曹植在立嗣竞争中败北,曹丕即位后对之一再贬徙。曹植从优游恬适的贵族王子,变成蹉跎坎坷的失意文人。这让他有机会更多思考社会与人生。在曹植笔下,此次瘟疫横恣,情况比建安初期张仲景的境况更惨,无妄之灾降临世间,无数民众惨遭横死,甚至满门阖户,无一孑遗,这是多么凄惨的人间悲剧!不过,曹植认为,受害最深的主要是粗衣陋食,蓬门筚户的贫民,而r肥马轻裘,锦衣玉食的权贵似乎影响不大。

东汉末年,在曹操统治区崛起了一座文学高峰——“建安文学”,这一奇特的文学现象,以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为核心,以“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七子”为星系,以邺城铜雀台为沙龙,形成了“雄浑深沉,慷慨悲凉”为特质的“建安风骨”。“七子”即曹丕所称的“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三曹集》,页178)刘勰的评论更为精审,“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404-405)刘勰骈文雅驯,说的正是“三曹”“七子”(中缺孔融)。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被操所杀,阮瑀早年病死,其余“五子”均死于此次瘟疫之中。王粲为“七子”之一,他不仅是曹氏父子器重的幕僚,也是“七子”中诗赋之冠。同样是建安二十二年,同样是征吴途中,因感染瘟疫而去世,时年41岁。(《三国志》,页599)翌年(218年)春,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写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三曹集》,页161)曹丕这封信透露了一个重大噩耗,即“建安七子”中在世的四人,即“徐陈应刘”(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均未能躲过这场瘟疫。由于这场大疫,曾经璀璨一时的文艺星空竟然众星陨落,令人唏嘘!应当指出的是,曹丕这封信透露的消息,与曹植关于疫病“远富近贫”的特征并不一致。瘟疫或病毒没有等级、领域、“三观”的区分与内定。在它们面前,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只要被感染,不管你是皇亲国戚,还是文坛巨星,同样在劫难逃。
应当指出的是,以曹丕当时的身份,他在对待文友的问题上,并没有任何居高临下之意,相反,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却是真挚醇厚的情谊,对昔日聚游酬唱的亡友深致哀痛,甚至为文友亲自编定文集,并对诸子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客观的评论。然而,吴质这位元城令,却在回信时对四位亡者太过苛求,“陈徐刘应,……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昭明文选》第4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页525)这无非是说,他们四人,虽富翰墨之资,却非经纬之才,不过御用文人而已。吴质的说法很不厚道。
其实,在瘟疫中失去生命的权贵何止这些文人。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中,司马懿之兄司马朗随军征伐东吴,瘟疫在军中流行,司马朗亲临视察,筹措医药,不幸感染,去世时只有47岁。他甚至留下遗言称:刺史“督司万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三国志》,页468)曹冲是曹操的小儿子,“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至今“曹冲称象”的故事家喻户晓。建安十三年,死于疾病,年方13岁,曹操因之“哀甚”。(同上书,页589)
臧否人事,褒贬是非,不是本文之旨。今人应当感谢的是,历史上举凡王权更替、朝代兴亡、皇纲盛衰,往往连篇累牍,而关乎民瘼、人心的事件,却向来不为史官所垂顾。人民无法书写历史。然而,在古代文人的残简断墨中,也许看到百姓生计的片言只语难,虽然这样的发现很偶然,却有可能揭示或一方面的历史事实。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