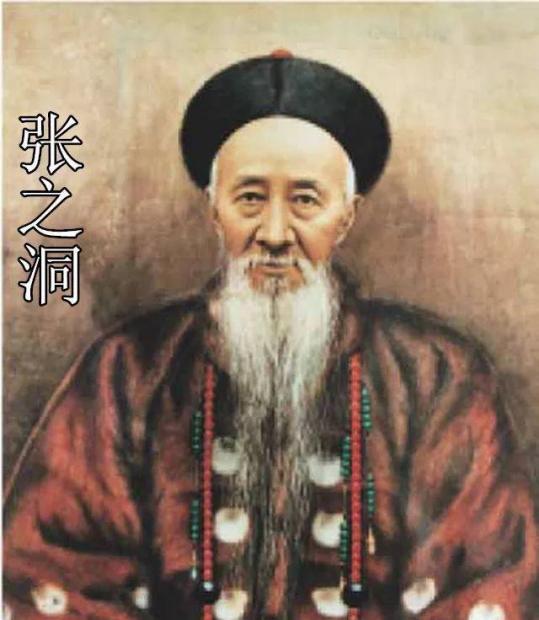
2014年4月,专程驱车到河北南皮拜谒张之洞墓园。墓园座落在双庙村北的麦田里,孤寂而冷清。这个生前曾位极人臣,死后(“文革”中)被掘墓抛尸的清末名相,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至今余响不绝。“中体西用”并非为了维新或立宪,“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0621)为维新与立宪设定底线,才是他的直接目的。

不能说他对贯彻这一方针没有诚意。张之洞是极看重名节的“清流”人物。他指出,“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同上,P9767)可见,他对“西学为用”认识是清醒的。然而,当他意识到“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同上,P10063)他也不免迷茫与徘徊。在“西学为用”上,似乎又表里不一。
张之洞一生建树,主要在洋务与教育。他在署任两江总督期间,主持一次经济特科考试,试卷是他“恭呈钦定”的,他握有一票否决权。“某本列一等,以卷中用鲁索语,降列三等,批语有‘奈何’二字。某自题诗,有‘博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试卷用鲁索’句。或曰即如皋冒鹤亭郎中广生也。”(《清稗类钞·考试》电子版)引文中人物需作说明,“南皮”即张之洞;“鲁索”今译“卢梭”,法国思想家;冒鹤亭后来成为中国文化闻人。只因在考卷中引用了卢梭的观点,本列“一等”的冒鹤亭,却被张之洞降级处理。如此作为,与其倡导的“西学为用”是否南辕北辙?其实,张之洞并非见西学而蹙眉,闻卢梭而横目。他在《劝学篇》中强调:“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张之洞全集》,P9721)冒鹤亭触了霉头,“盖香帅以卢梭主张民权,故深忌之。”(1903年7月19日《大公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言行不一。
甲午战后,日本侵入中国,“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辄之以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清稗类钞·讥讽》电子版)有人题诗讽刺道:“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同上)每句都含日本汉字名词。作为“西学为用”的组成部分,如何借鉴日本文化,张之洞是制订了优先政策的:“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全集》,P9738)这是张氏之说,再看张氏之行。“张孝达(之洞)自鄂入相,兼管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云:‘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趋庭随笔》卷三,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P7)不久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张以‘检定’二字为嫌,思更之,迄不可得,遂搁置不行。”(同上)只因拿不出确切的中国词语替代这句“日本土话”,竟然把正事都耽搁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张抵制外国语词,是基于其深藏心中的精神律令与文化桎梏。不过,他最终闹出了笑话:张之洞“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1998年电子版)这个下属居然对其上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够牛!
张之洞曾对“西学”包括的“西政”和“西艺”作过明确界定。然而,此类外来语,既不属于他所极力抵制的议会与民权这类敏感词,也不属于“西政”、“西艺”的任一内容,而这似乎是他在撰写《劝学篇》时所不曾想到的。
此时的中国,因不断割地赔款,已是内外交困。枪炮船舰相形见绌,典章制度也不如人,国人引以为傲的似乎只剩下语言文字了。于是,语言文字担起了捍卫“中学为体”的历史重任。不过,当时一些清醒的士人并没有刻意拔高语言文字的地位,严复在致梁启超的信中指出,“文辞”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P516)他把语言文字仍然置于交流工具的范畴。在他看来,所谓“文以载道”,“道”才是“本体”,“文”只是“载体”。一些学者却不这样认为,邓实指出:“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P173-174)语言文字竟然成了关乎国家存亡的利器。不仅如此,如何使用语言文字,也成了衡量士人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1903年,清廷颁布《学务纲要》云:“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可见,官方已将文法字义的变化,上升到国运兴衰、风教存亡的高度。无论是朝廷曾经出台的正式文件,还是国内士人“学之将丧,文必先之”的愤激之语,主持全国学政的张之洞不会不清楚,作为主政者,他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
1907年,张之洞就创立存古学堂一事上奏朝廷:“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张之洞全集》,P1762)从而确立了基本立场。大量外来词汇进入清廷官方的文牍系统,这让张之洞忧心忡忡,此时他担心的不再是“西学”应否“为用”的开放问题,而是“中学”如何“为体”的稳定问题。于是,1908年2月1日,《盛京时报》刊出这样一则报道——《张中堂禁用新名词》:“闻张中堂(之洞)以学部往来公文禀牍,其中参用新名词者居多,积久成习,殊失体制,已通饬各司,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通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以存国粹。”由此可见,正是张之洞开创了动用行政权力干预语言文字的先例。
汉语言与外来语已经争斗了上千年,争斗之形式,无非战争、商业、文化诸端。在古代,对汉语影响最大者,源于佛教和西域,即使在我们今天的语言里,仍然充斥着大量佛教用语(如“过去”、“现在”、“未来”、“自觉”、“世界”、“境界”、“宗旨”……)和西域用语(如“胡同”、“戈壁”、“葡萄”、“琉璃”、“琵琶”、“骆驼”、“胡琴”……)而不自知。近代以来,日本的汉字词语大量涌入我国,前引的讽刺诗即为一例。当代更有大量欧洲语言的音译词汇如“咖啡”、“巧克力”、“沙发”、“雷达”、“因特网”、“模特”……进入汉语。土著语言与外来语言的争斗仍在继续,每一次争斗的结果,都为汉语注入了活水,增强了汉语自身的生命力。其实,纯洁并非语言的第一要义。封闭的语言系统可能最纯洁,然而它却是一潭死水。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有关方面指令,为“保护汉语”之纯洁,禁止外语缩略词如“NBA”、“GDP”等进入媒体。此事曾在网络引起热议。有人反驳说,要废除汉语中的外语缩略词,首先应废除阿拉伯数字,这是最早出现的与汉字造字原则与形体结构完全不同的外来语言。人们无法想像,日常生活中,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如GDP、CPI、PM2.5、Wi-Fi,换成汉语是多么繁琐与别扭。当年张之洞要求人们“通用纯粹中文”,却连自己使用“日本土话”而不自知,这样的指令与投鞭断流又有多大差异?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