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飞之孙岳珂)
我向来认为,后人对于前人,尤忌溢美与抹黑。恶者不因溢美而善良,善者不因抹黑而邪恶。反之,溢美之于善者,无疑于佛头着粪,抹黑之于恶者,倒近乎制造疑案。不论治史还是论人,均应以客观求实为旨归。
岳珂作为岳飞的嫡孙,他在整理其祖父的史料方面,下过一番搜遗辑录之功夫。但在其编著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中,却不止一次地对其祖父滥用化妆术——他隐瞒了岳飞的贫寒家世,称其出身于书香翰墨之家;歪曲了岳飞中原作战的进军史实,臆造了一场子虚乌有的“朱仙镇大捷”;颠倒了“良马论”的对话主体,将高宗赵构与其祖岳飞身份倒置。如此等等。(参见邓广铭《岳飞传》)
如果说岳珂对于岳飞的化妆,是出于后裔晚辈情感的话,只能说明其治史态度,感情混淆了客观,血缘代替了公正。这对于岳飞这样一位在当时乃至后世均已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这就是佛头着粪的道理。如果说此类化妆施于他者而当别论的话,那么,如果在其著作中找出自我粉饰的例证,就是立身处世问题了。
邓广铭先生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中,曾引用一则宋人笔记,以此说明辛稼轩(弃疾)的创作态度。这则笔记即来自岳珂的《桯史》。邓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岳珂这段笔记是作为正面论据引述的。

(辛弃疾)
这是一则评论稼轩词的笔记。稼轩先生对《贺新郎》与《永遇乐》两阕甚为自许,“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孙谢不可。”对于《贺新郎》,岳珂的记述是,稼轩“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另一首“新作”《永遇乐》,开禧元年春(公元1205年)作于镇江知府任上。其中有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首词不仅充满了豪迈雄浑之气,而且对南宋政权的对金战略表示了忧虑。明人杨慎赞曰:“辛词当以京口北固怀古永遇乐为第一。”(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五引《升庵词话》)信为确评。
此时的岳珂年方22岁,此前只是负责户部军仓的基层干部,在一次官员考试落榜后,被辛弃疾招入幕府。岳珂在“回忆录”中如何描写辛弃疾这个长官与长者对他的印象呢?在稼轩先生要求来宾对其词作“摘其疵”之时,本来只是“偶坐于席侧”的岳珂,开始略作谦虚,后来竟语出惊人:“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他真把自己当作稼轩先生的“一字师”了。在岳珂笔下,稼轩听了他的议论,不仅不以为怪,反而喜出望外,竟“促膝亟使毕其说”。岳珂也就不谦虚了:“前篇(指《贺新郎》)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指《永遇乐》)微觉用事多耳。”在岳珂的“余曰”中,前者是指《贺新郎》上片结句“情与貌,略相似”与下片结句“知我者,二三子”。后者是说《永遇乐》一阕用典偏多,有“掉书袋”之嫌。辛弃疾对岳珂的意见“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575)意思是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切中了我的要害。不过,这一切都出于岳珂的一面之词。
当今在国际场合只有自家的讲话才是“重要”的,岳珂的意见似乎也成了这类“讲话”。由于岳珂的意见特别中肯,于是稼轩即据其意,“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令人不解的是,南宋迄今,多个版本的《稼轩词》,偏偏是《贺新郎》与《永遇乐》两阕,只句未改,片字未易。岳珂不是说稼轩因他的意见反复修改了么?难道岳珂在扯谎不成?邓广铭先生“不无遗憾”地指出,岳珂“确实为了炫示自身如何受到辛稼轩的重视,而特地写此一段扯谎文字的。”这“炫示自身”不正是“自我妆扮”的同义语么?
在治史中,对他人或自身使用化妆术,岳珂当为显例,前曾为其祖化妆,后又为自身粉饰。邓广铭先生的结论是在《后记》中增补的,考虑到“引用《桯史》这段记事而论述辛词者,都大有人在,可见误信岳珂此言者正复不少”(《稼轩词编年笺注·略论辛稼轩及其词(附:后记)》),邓先生不仅没有删去前文的引述,而且专门增补此一《后记》,以揭穿其化妆术。当然,这也是一种治史态度。
0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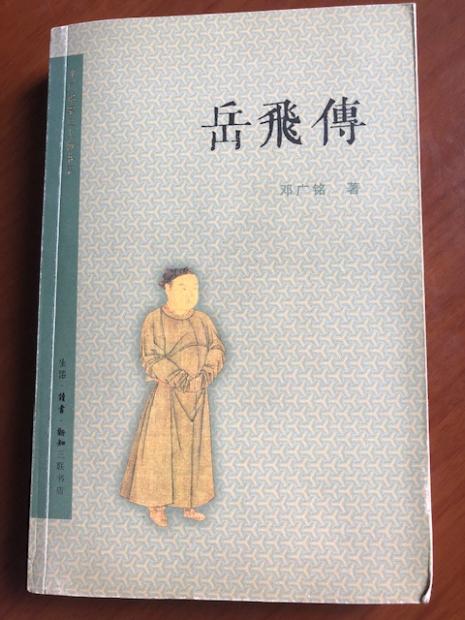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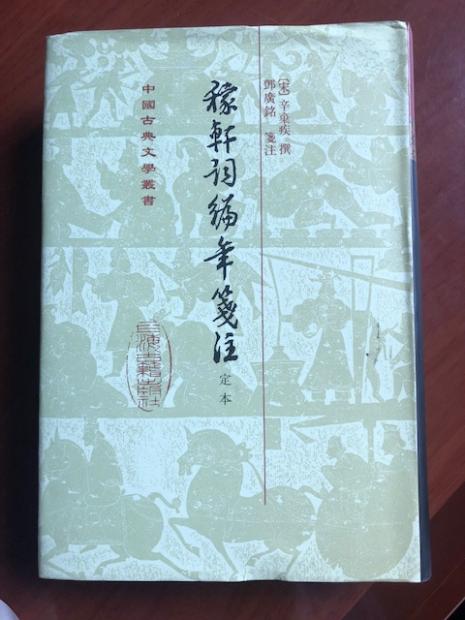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