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手记之一

今年是隋炀帝驾崩1400周年。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是一个争议人物。此人的执政实践,究竟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至今聚讼纷纭。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官方史书比如《隋书》和《资治通鉴》中,隋炀帝的形象基本是负面的。对杨广的记叙与评价,前者较之后者,似乎平和与客观一点。本文没有对史书进行证实或证伪的企图,只是就史书记载写下一些随感而已。
杨广在位14年,如同许多试图青史留名的帝王一样,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浮夸虚荣,表现的更为突出与典型。他的文治武功,可以粗线条地概括为三句话,即大举兵戈、大兴土木、大肆巡游。正是由于他经年累月的瞎折腾,不仅给百姓生活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也给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混乱。民不聊生与社会混乱,是导致民怨沸腾、民变蠭起的社会基础与前提。于是,各地民众揭竿而起,评书上说,“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在这个重大历史变迁过程中,有人否认唐代隋祚的说法,意思是说,隋末政局早已失控,天下不复为杨广所有,唐朝并非直接推翻隋朝,而是收拾天下乱局的结果。

以隋王朝当时的国力,百姓出现了愤怒与反抗,国家出现了乱局与动荡,只要正视问题,找出原因,对症施治,并非不能挽回。然而,恰恰相反,朝廷上下不仅不肯正视国家与社会的危机,而是相互欺骗,闭目塞听。在上者,陶醉于辉煌与繁荣之中,不愿听闻扫兴与失败的信息;在下者为邀宠固位奉迎谄媚,报喜不报忧,以致野火肆虐、浊流横溢,最终局势失控,不可收拾。抛下首都不顾、躲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的丹阳宫里醉生梦死的这些昏君佞臣,未待各路叛军杀到,就已在宫廷反叛势力的刀下死于非命。
大业十二年(616)五月,杨广也曾询问过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叛乱情况(即“贼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是如何报告的呢——“渐少。”杨广问:“比过去少多少?”如同今天的房价一样,起码要告诉一下“同比下降”或“环比下降”的幅度吧?宇文述竟然极力大事化小——“不能什一。”意思是说,目前的贼情,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5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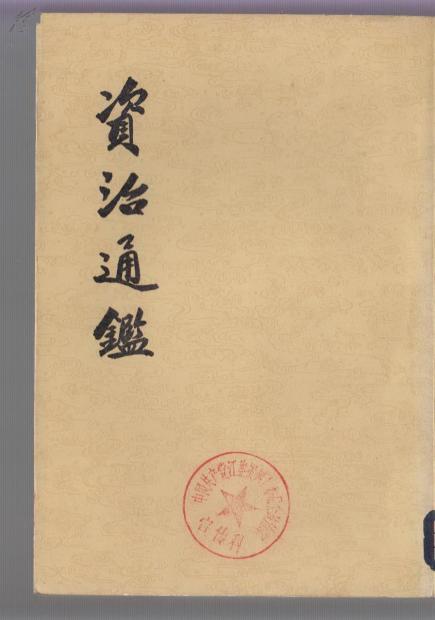
“纳言”这个职务本来就是向皇上提供参考意见的。身任此职的苏威却躲在柱子后面,杨广把他叫到阶前询问同样的问题,苏威回答说:“我不分管此事,不知到底有多少,只是贼患距京城日益迫近(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渐近)。”杨广问:“什么意思?”秉性耿直的官员,往往掩饰不住话语的锋芒,苏威终于漏出了实话:“过去盗贼只占据长白山(今山东济南东——笔者注),如今已近在汜水(今河南洛阳东——笔者注)。况且往日的租赋丁役现又何在呢?不是都变成盗贼了吗?近来看到的贼情并非实情,因此措置失当,不能及时剿灭。还有,此前在雁门曾经许诺停止征伐辽东(指高丽——笔者注),现在又征发士兵,盗贼怎能平息?”苏威其人,无论出于职责所系,还是出于人性所使,毕竟道出了实情。他指出,过去守法纳税的百姓,也已加入叛军行列。他甚至直接批评朝臣报告贼情不实,以及朝廷的政令失信。对于这样的意见,杨广显然很不受用。(《资治通鉴》,页5703-5704)
当年五月,杨广就征伐高丽事征求苏威意见。苏威想借机让皇帝了解天下贼情的真实情况,他建议说:“现在征辽之事,但愿不要发兵,只要赦免群盗,就可得到几十万人,派他们去东征,这些人因被赦罪而高兴,会竞相立功,高丽就可以被平灭。”苏威这个赦免群盗、使之从军的建议,触怒了杨广的虚荣心。苏威出去后,见风使舵的御史大夫裴蕴对杨广说:“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杨广也忿忿然:“这老猾头,以贼来威胁我(老革多奸,以贼胁我)!”裴蕴揣知了皇帝心意,遂使人诬告苏威。杨广一怒之下,把苏威削职为民。不久,苏威就被裴蕴寻机处死。(《资治通鉴》,页5704)
大业十二年(616),是隋朝政权的多事之秋。全国各地因官逼民反而起义、叛乱风起云涌、警报频传。整天揣摩上意的内史侍郎虞世基,对于杨广“恶闻贼盗”的心态十分清楚,于是,他利用职权,对所有的贼情报告予以扣押或删改,从不据实上报(“世基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他向皇上报告的口径总是:“鼠窃狗盗之徒,郡县官吏搜捕追逐,快要被彻底消灭了。希望陛下不要放在心上!”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的杨广竟然信以为真,对于那些敢于报告叛乱实情者,“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杨广制伏“妄言”的资格更早——笔者注),由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资治通鉴》,页5715)当人们的嘴巴被贴上封条之后,也等于堵上了皇上的耳朵!
杨义臣是一名能干的地方官员,击败并收降了河北贼众几十万,他把情况写表上奏炀帝。这显然是一封奏凯捷报。报喜得喜,按说没有什么忌讳。然而,杨广却读出了不同的味道:“我原来没听说盗贼到如此地步,杨义臣降服的贼怎么这样多?”的确,这则破贼捷报,无意中戳穿了长期以来虚假的“盛世”与“繁荣”,何以河北一地叛军竟达数十万,这显然超出了杨广的心理预期。为了继续欺骗下去,虞世基竟然向杨广如此解释:“小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他不仅极力缩小河北叛军的规模与危害,并极力贬低此次大捷的意义与作用,反而提醒皇上要警惕杨义臣手握重兵的危险性。杨广居然听信了谗言,他所担心的并非迫在眉睫的叛乱,而是部下的忠诚。他对裴蕴的提醒十分赞许:“卿言是也。”于是,即刻削弱杨义臣的兵权,解散其部队,“贼由是复盛”。(《资治通鉴》,页5715)
应当说,在隋朝覆亡的最后阶段,朝廷不乏清醒而忠诚的官员。他们不顾职务去留与身家性命,毅然上报朝廷,警醒即刻面临的危机。治书侍御史韦云起看到虞世基和裴蕴欺上瞒下的行径后,随即上奏杨广:“虞世基和御史大夫裴蕴负责机密枢要,掌管国家内外大事,现在四方告急,却不上报,盗贼数量如此之多,他们却修改删减表报,陛下听说贼少,也就发兵不多,双方众寡悬殊,征讨不能取胜,官军因此失利,贼党却日益增多。请将二人交付有关部门追究他们的罪过。”大凡国家危难之际,谗佞之徒往往结党营私,甚至成为朝廷内部一股无可挽回的消极势力。果不其然,对于韦云起的忠直建言,本当主持正义的大理卿郑善果,官官相护,狼狈为奸,诬告韦云起“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威权。”杨广居然听信这样的诬告,随即将韦云起贬为大理司直,置于郑善果的辖治之下。(《资治通鉴》,页5715)
在隋炀帝横死的前一年,叛军包围了东都洛阳。杨广之子、越王杨侗派遣太常丞元善达,穿越叛军控制区,九死一生赶赴江都报告贼情:“李密拥兵百万,包围进逼东都(洛阳),占据了洛口仓,东都城内已经缺粮,如果陛下迅速返回东都,乌合之众就会溃散,否则东都定会陷落。”此时的杨广,大抵出于父子之情,听完报告,不免动容(“因唏嘘呜咽,帝为之改容”)。又是这个虞世基,竟然如此劝解皇上:“越王年少,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杨广果然听信谗言,勃然大怒;“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即刻下旨,令其再度穿越叛军控制区,向东阳催运粮草,不出预料,元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是后人人杜口,莫敢以贼闻”。(《资治通鉴》,页5728)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意味着末日即将来临。
东都洛阳被叛军占领,首都长安更回不去了。此时,整个黄河流域,已是处处烽火,遍地王旗了。更为糟糕的是,杨广的皇位已被李渊废黜,让其13岁的儿子杨侑当了傀儡皇帝,是为隋恭帝。叛军尚未杀到江都,杨广的御林军——骁果军发动了兵变。此时的江都局势,岌岌可危、十万火急。一名宫女向萧皇后报告:“外面人人想造反。”萧后答复:“你去报告皇上吧!” 宫女便告诉了皇上,杨广很生气,认为这不是宫女该过问的事,报告者最终被杨广“斩之”。其后,又有宫女向萧后报告,萧后无奈地说:“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资治通鉴》,页5777)
皇权专制之下,暴君与佞臣如影随形,相伴而生,到底是暴君滋生了佞臣,还是佞臣造就了暴君,不得而知。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已被骁果军挟持的杨广,皇冠落地,还在计较待遇,叛军让其乘马进殿,他竟然“嫌其鞍勒弊”,要求“更易新者”。此时,杨广想起了他的贴心“近臣”,“(虞)世基何在?”答曰:“已枭首矣!”此时,杨广的宠臣虞世基、裴蕴等均已被杀。死到临头的杨广竟然问道:“我何罪至此?”一叛军首领答道:“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杨广可能认为眼前这些人都是身边工作人员,都属既得利益集团,为此,他辩解道:“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另一首领道:“溥天同怨,何止一人!”(《资治通鉴》,页5780)
魏征以《隋书》的编纂史臣的身份,曾对杨广恶闻贼情的施政弊端作出评论:“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96)大厦将倾,闭目塞听,置若罔闻,只顾追求表面风光与短期繁荣,国家出事就在劫难逃了。《隋书》也对隋炀帝这一恶行作了强调:“区宇之内,盗贼蜂起,……近臣互相掩蔽,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悟也。”(同上书,页95)
这个“肃膺宝历,纂临万邦”的大隋天子,明明知道“非天下奉一人”,却自信地“乃一人主天下”,最终因为一意孤行、罔顾民意,而被人民所唾弃;这个刚愎自用、妄自尊大的暴君,整天佞臣围绕、颂声盈耳,在其治下,怨声载道,饿殍遍野,无数冤魂怨鬼,都被关在九重门外,到死都不明白,他何以落得如此下场!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