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乌托邦”这个词,始于年轻时的两次学习运动。一次是在中学时。1970年批陈(陈伯达)整风时,领袖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并指定学习马列六本书(《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作者注),“文革”的中学生的水平,读这些原著,囫囵吞枣,似懂非懂。一次是在入伍后。1975年初,我在连队当文书兼军械员,随同指导员参加团里的理论学习班,学习中央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叫“33条语录”)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作者注)。回到连队给战友讲解“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这两次学习都涉及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欧文(英)、圣西门、傅立叶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作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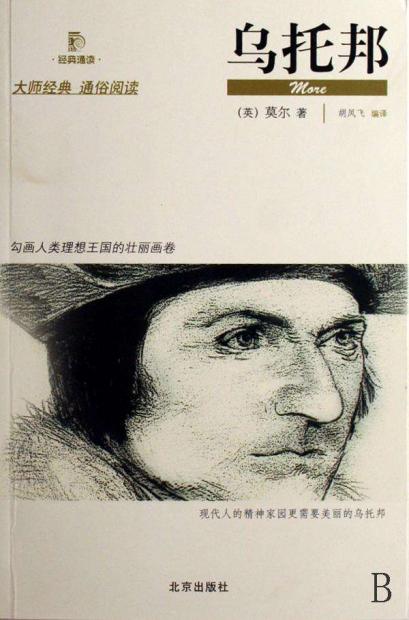
提到空想社会主义,自然提到莫尔的《乌托邦》。乌托邦(Utopia)的本义是“没有的地方”,其引伸义是“虚构的国家”或“空幻的理想”。16世纪之后,欧洲诞生了一大批乌托邦式的作品,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得里亚的《基督城》、哈林顿的《大洋国》等,都属这一性质,其实更早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学术思想上也充满了乌托邦色彩。我国古代没有如此规模的乌托邦文学,但并不缺乏乌托邦作品,在年代上,也比西方早出许多,比如上古时代黄帝梦游的“华胥国”,东晋时期陶渊明误入的“桃花源”,就是这种类型,这也是我们“祖上阔过”的又一证据。另外一些不成体系的作品,比如《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也可归入这一类。
这些作品和学说,反映了人们对于幸福、美好、自由、人性的向往与憧憬,尽管这些“地方”、“国家”、“理想”只是子虚、乌有或亡是公。人们之所以产生这种虚幻、空想而又美好、幸福的向往,不仅与人们凄楚苦难而又难以救拔的生存环境有关,也与人们一厢情愿的思维逻辑有些关系。人们总是认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人类社会总是进步的、前进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们的思维逻辑中,“昨天——今天——明天”的关系,就是“黑暗——隐忍——光明”的关系,甚至是“不好——较好——更好”的关系。跳脱阿鼻地狱,必然到达极乐世界,佛教的因果报应信众芸芸,就是明证。这样的思维逻辑,王蒙先生称之为“历史乐观主义”,他指出,有人甚至将“历史乐观主义简单化——变成简单机械的历史进化主义,即简单地认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美丽新世界》前言,重庆出版社,2005年)
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仍然把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只能是五种,决不能是四种以下或六种以上,而且一定是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环环相扣,步步登高,如同上帝预先设定的电脑程序,人类社会只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按照程序运行。先不说它对未来社会不可能未卜先知,历史的履痕已经证实,社会发展并不是按照这种程序运行的。奥裔英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批判隐藏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与苏联暴政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时,把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极权主义元素称为历史主义,他指出:“某些有影响的历史主义作家曾经乐观地预言过自由王国的到来,人类事物在其中能够合理地加以规划。他们教导说,由目前人类遭受苦难的必然王国向着自由与理性的王国的过渡并不能靠理性来实现,而——奇迹般地——唯有靠严峻的必然性,靠那种在劝导我们要屈服的盲目而又无情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页85)这个“自由而理性的王国”其实就是乌托邦,它如同在浩瀚无垠的河外星系筑造了一块固定而美丽的人工岛礁,并且要求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多少光年才有可能到达的飞船相信,你会确定无疑地找到这块人工岛礁,于是你就会到达你所憧憬的“自由而理性的王国”。然而,人们一般认为,找到这块岛礁根本没有可能,除非这块岛礁为上帝所设定,除非这只飞船由上帝来驾驶。
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是清醒、理性人士的看法。所谓“波浪式”、“螺旋形”,即意味着将会遭遇波折与坎坷,将会出现逆流与倒退。即使如此,人类社会还是“前进”与“上升”的,因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成了一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鼓舞人心的固定模式,甚至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话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这句名言人们耳熟能详:“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然而,波普尔对马克思这一名言并不赞成:“马克思总结出的这个公式,极出色地表现了历史主义的立场。虽然它既未教导无为也未教导真正的定命论,但是历史主义却教导说,任何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的企图都是枉然的!这仿佛是定命论的一种特殊的变种,一种有关历史趋势的定命论。”(《历史主义的贫困》,页86)既然“明天更美好”、“未来更光明”,而且是客观规律,是命中注定。那么,除了一些理想型或拍马型文人之外,一些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与利益,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构思、描绘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告诉人们,在那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在那根本不知尽头的地平线,有那么一处美好的所在、有那么一个幸福的国度、有那么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有那么一座蓬瀛仙岛,只要把人们的向往与憧憬成功地转移到那个方向,人世间一切人为的灾难、蓄意的罪恶、邪恶的暴力,都被掩盖了、被淡化了、被转移了,人们即使不得不消受、忍耐、苦撑这些灾难、罪恶与暴政,也是抵达美好彼岸、实现乌托邦的必要成本,“受得苦中苦,定为人上人”,“此世既为鬼,来世必成仙”。“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谁能说的清“波浪式”不是剧烈的社会动荡,谁能说得清“螺旋式”不是严重的历史倒退?谁能保证“波浪式”只是几度春秋?谁能保证“螺旋式”不是岁月漫长?“春秋”与“岁月”对于历史长河只是一瞬,人生在世,有几个“春秋”与“岁月”?多少人会因这种波折与逆转而白骨露野、化为烟尘?
然而,历史乐观主义与历史悲观主义是并行不悖的,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明天会更好”、“未来更光明”,怎么可能排除“明天更糟糕”、“未来更黑暗”,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悲惨局面。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未来不一定比现在更好,“今天的一切未必事事胜过昨天,而明天的一切也未必事事强似今天。”(《美丽新世界》王蒙前言)魏玛共和国的公民怎么可能想到,新社会(纳粹德国)比旧社会更黑暗;柬埔寨王国的臣民怎么可能想到,新制度(红色高棉)比旧制度更残暴;自由与面包都不充裕的旧俄国(沙皇俄国)的国民怎么可能想到,在新俄国(红色俄国)自由与面包更加严重短缺?正因如此,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在写了、读了大量乌托邦作品之后,在他们敏锐的笔下,又开始了敌托邦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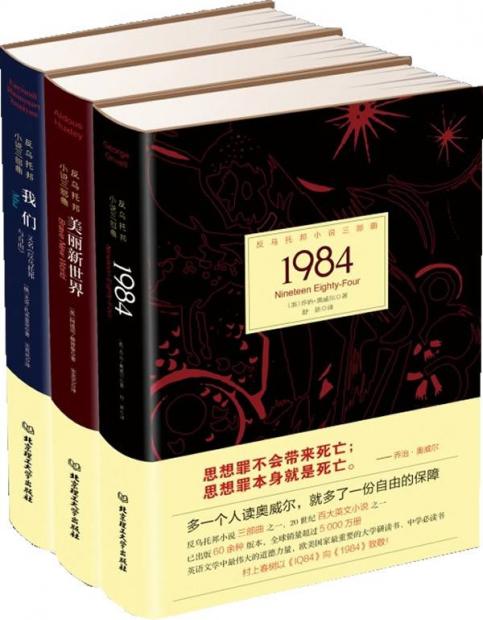
“敌托邦”,是我刚接触到的概念,也就是以前听说过的“反乌托邦”或“反面乌托邦”。敌托邦与乌托邦相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描写的不是一个美好、自由、人性的理想世界,而是一个邪恶、恐怖、无人性的世界。如果说,人们创作乌托邦文学,体现了人类对于幸福、自由的追求与憧憬,那么人们创作敌托邦文学,则体现了人类对于邪恶与极权的恐惧与悚惕。二者作为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关切,其实并无二致。波普尔指出,“人们把人类历史看作进步史的‘观点’就不必然与那种把人类历史看作是退步史的观点不相容,……我们既能够写一部朝向自由的进步人类史(例如包括反对奴役的过程),又能写另一部倒退和压迫的人类史(也许包括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影响这类事情)。这两种历史不仅并不冲突,而且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就像从不同角度看同一风景而看到两种景色一样。”(《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403-404)从他这一观点看来,乌托邦与敌托邦,不仅同样重要、也同样必需,二者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有人说,乌托邦是原版,敌托邦是影印件,而且永远是黑色的影印件;乌托邦是正面描写,敌托邦是负面响应;乌托邦是清晰的镜象,敌托邦是扭曲的影像;乌托邦是未来的天堂,敌托邦是黑暗的地狱。这种说法,如同当下硬生生地把只有大小而无正负的能量分为“正能量”、“负能量”一样,其实带有十分浓重的情感好恶与主观偏爱,其基本立场是倾向、向往前者,而否定、厌恶后者的,论者并不知道,敌托邦所描述的社会本身也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会是一种历史事实。
在许多人看来,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这些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极具洞察力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科技的发展,其作用具有两重性,它们并不必然地给人类带来幸福、自由与人性,它们有可能成为极权主义者控制人们的手段和工具,从而加剧人们的恐惧与痛苦,并在新的层面上剥夺人民的幸福与自由。20世纪以来,陆续涌现了一批敌托邦文学作品,比如苏联作家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创作于1921年的《我们》,描写的是26世纪生活在“唯一国”的人类;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创作于1931年的《美丽新世界》,描述的是福特纪元632年(公元2532年)的宇宙国;另一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于1948年的《一九八四》,它瞻望的是“二战”结束几十年后的人类政治与社会生活。《一九八四》以抨击极权主义的控制为主,《美丽新世界》揭示了统治者如何利用科技扭曲人性。而作为敌托邦先驱的《我们》,则兼顾了这两个不同的角度。这三部作品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人们之所以看重这三部作品,并不是其他类似作品不值一提,而是这些作品揭示了未来社会可能产生的弊端确有代表性。
如果说,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上分析乌托邦与敌托邦的产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宏观性与外在性,那么,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乌托邦与敌托邦的产生,显然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微观性与内在性。“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作为一个久远的哲学话题争论了几千年,其实,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产物,作为地球上的高级灵长类,具有善恶的双重属性。人类社会涉过漫长的历史长河,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辉煌的人类文明,当然是人性之善结出的硕果。反之,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经历如许之多的残酷、丑陋和野蛮,遭遇如此之多的战争、暴政、屠杀、迫害与冤狱,正是人性之恶造成的恶果。如果说乌托邦文学产生于人性美好善良的一面,那么,敌托邦则产生于人性丑恶黑暗的一面。正因为人类执著地追求真善美,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乌托邦文学;正因为人性中存在着邪恶黑暗的冲动,才使世界变得丑陋、残酷、邪恶,才会产生敌托邦文学。
然而,上述说法并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指出的是,乌托邦文学的作者未必就是人性善的典范,敌托邦的作者未必就是人性恶的化身。有时恰恰相反。一些作者正是由于其人性之恶,才会对于人类苦难置若罔闻,对于政治邪恶着意逢迎,如同鲁迅所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热风·随感录三十九》)拼命编织美妙的乌托邦。另外一些作者,正是基于人性之善,才会对人类可能的苦难命运,抱以特别的警觉与悲悯,而这些正是一些敌托邦文学的创作动因。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