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动物农场》随记之七

前几年,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曾有一篇奇文——《中国动物各阶级的分析》,在文艺界产生过很好的反响。最近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译文出版社,2003年),我突发奇想,假如对动物进行阶级分析,动物农场的成员们其实是极好的分析对象,尽管它们标榜所谓“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分析结果肯定与它们的标榜大异其趣。
对动物进行阶级分析,当然免不了对动物的褒贬问题。这使我不禁想起一件民国旧事。湖南长沙有一前清遗老叶德辉,在藏书、版本诸领域颇有名气。此人虽满腹经纶,但却性情孤傲。1927年,痞子运动风起云涌,时任湖南总商会会长的叶德辉为之题联曰:“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满堂。”横批:“斌尖卡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竟敢骂农会是杂种、畜生,叶德辉终于活到头了。叶德辉提到的六畜,其实正是动物农场的基本成员。他对这些动物并无褒贬之意,只因他将畜生拟人,才招来杀身之祸。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这些动物造反前后的境遇并没有多大改变。老少校临终前启蒙这些动物们,“咱们的生活非常痛苦,劳累不堪,而且极其短暂。……那些能够干活的,……一旦精力枯竭,没有用处了,就被残酷凶狠地屠宰掉。”(《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页309。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老少校分析了自身悲惨命运的根源:造反前,奴役动物的是人类,是琼斯先生,“他逼着牲畜们干活儿,劳动所得,他只给回一点点刚刚不至于叫他们饿死的数量,剩下的全部据为己有。”(页310)老少校没有机会看到,造反后,动物仍然受奴役,不过,此时的奴役者却是它的同类——猪集团。这个灰白色的老公猪批评人类是“唯一只消费而不事生产的生物”,“他不会产奶,不会生蛋,他毫无体力,不能拉犁,他跑得不快,捉不到兔子。但是他却成了所有牲畜的主宰。”(页310)驱逐琼斯之后控制了动物农场的伯克夏公猪,岂非同样如此!在这里,如果把老少校批判的对象,从琼斯换成拿破仑,从人类换成猪,也同样合适——只是其他动物的命运依然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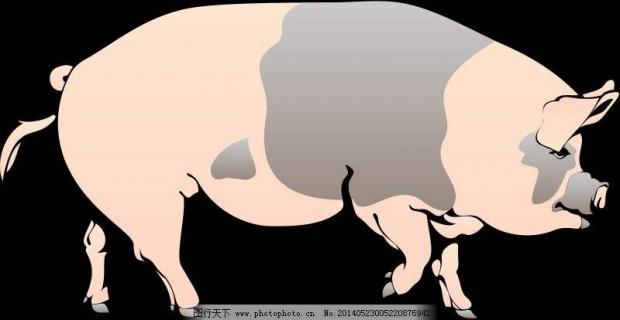
在动物农场里,统治阶级是猪家族,狗则是猪的保镖或帮凶。毛驴本杰明、山羊穆瑞尔则是慑于拿破仑的淫威而不敢说话的有点文化的动物。两匹辕马拳击手和苜蓿则是农场最勤恳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大多没文化,脑袋虽没被驴踢过,但它们的脑容量太低,大概与脑残相差无几,经过三个月培训,苜蓿只认识26个字母,却不会拼成字;拳击手只记住了ABCD,后面的再也记不住;羊、鸡、鸭等成员,最终也只认识了A。正因如此,它们连七戒也记不住。雪球为了方便它们学习和领会,只好把七戒概括成两句语录——“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语录很简单,也很精辟。那些低端动物对动物主义不感兴趣,只要背会这两句语录,也就掌握了动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两句语录几乎成了绵羊的最爱,它们刚在草地卧下来,就开始“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咩咩地叫个不停,是防止忘却的背诵,还是指导行动的惕励,似乎兼而有之。
动物们原来以为,造反成功了,翻身解放了,动物自主了,它们从此站起来了,奴隶变成了主人,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殊不知它们却陷入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循环里。一些动物成了新的奴役者,一些动物成了新奴隶。鲁迅在分析人类社会的奴隶时曾经指出:“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604)动物农场也是这样,那四只勇敢反抗拿破仑倒行逆施与错误决策的小猪,那九只消极抵制拿破仑杀鸡取蛋、巧取豪夺的母鸡,自然都是奴隶,虽然它们的反抗付出了鲜血与生命,但它们仍然不失为有骨气的奴隶。

而拳击手这匹老马则不同,它经历过庄园农场之旧,感受过动物农场之新;见识过庄园农场的人类,接触过动物农场的猪猡;它曾经为捍卫动物农场流过血,也曾为建设动物农场流过汗。只是它的智力不足以分析庄园农场与动物农场的优劣,它的头脑不足以分辨雪球与拿破仑的善恶。尖嗓花言巧语,拳击手拙嘴笨舌,它没有能力拆穿,顶多将信将疑。既然无法把握命运,只好听天由地;既然无法左右局势,只好盲从顺势。它只记得老少校的那些教条,却不理解那些教条的含义。它有时感到事情不应这样,真相并非如此,要想弄清真相和道理,它又缺乏能力,只好休息稀缺的脑细胞,干脆选择服从和看齐。拳击手对于拿破仑似乎真正达到了“相信以至迷信的程序,服从以至盲从的地步”。它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动物农场,却不仅遭到拿破仑帮凶的欺凌,也曾遭到拿破仑喉舌的威胁,然而,它竟然确立了这样的处世哲学:“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是正确的。”这匹老马被拿破仑榨尽了最后的油水,油尽灯枯之际,它羸弱老迈的躯体竟被拿破仑送给了屠宰场,并为其换回了一箱威士忌。拿破仑不仅伪造了它如何为拳击手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条件,也伪造了它如何为其支付了巨额的医疗费,试图让其他动物相信,它对拳击手的关怀是如何无微不至,它更不会忘记伪造拳击手向其表达忠诚的最后遗言——“拿破仑同志万岁,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页385)

可怜复可悲的是那些绵羊们,它们有着奴隶的命,却操着主人的心;它们吃着羊栏的干草,却思考着猪圈的大计;它们处于最低端的地位,却想着最高端的宏图。它们把被洗脑当作隆遇,被欺骗却甘之若饴;它们背诵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语录,却不知其确切含义。它们把服从拿破仑、维护拿破仑当成义不容辞的天职,把盲从和冲撞当成最高尚、最正义的行为。它们没有拳击手服务农场的本领,作不出拳击手曾经作出的贡献,也根本不曾获得拳击手曾经的荣誉,当然最终也难逃同样被出卖、被屠宰的命运。然而,在动物农场里,却没有谁“哀其不幸”,更没有谁“怒其不争”!
在拿破仑与雪球的权力斗争中,这些绵羊几乎全部接受了拿破仑的拉拢,它们感恩拿破仑的信任,它们讴歌动物农场的幸福。开始时,它们不分时间、场合,动不动就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会场上常常弥漫着它们杂乱无章的咩咩乱叫。动物们发现,每当雪球讲到关键时刻,绵羊就制造“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噪声污染(页337),从而干扰了雪球的演讲,破坏了雪球的议程。绵羊竟然成为拿破仑的同盟和工具。
拿破仑驱逐了雪球,废除了动物农场的民主大会,建立了由它独断的决策机制,遭到了四只小肥猪的反对。它们刚刚提出不同意见,不仅拿破仑的恶狗们发出了吓人的狂吠,这群绵羊也大声咋呼“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小猪的反对终于淹没在嘈杂的绵羊叫声里(页342)。已经控制动物农场的拿破仑,公然违反动物主义,试图与人类做生意。那四只正直的小肥猪刚想表示反对,又受阻于恶狗的利齿与绵羊的骚扰。那些绵羊根本不懂,它们口中嚷嚷的“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正是被拿破仑践踏与破坏的信条(页347)。
拿破仑在动物农场实行独裁统治,但它并未禁绝一切游行集会,所有为其歌功颂德的游行集会都是允许的。所谓“自发式的游行集会”,无非是庆祝各种辉煌与胜利而已。在指定的游行时间,动物们放下手中工作,在农场的院子里一圈圈地列队走步。绵羊们对参加这种游行集会热情最高,如果有谁对此发出怨言(当猪狗都不在跟前的时候,个别动物还是要发发牢骚的),绵羊们就大声高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从而把怨声压下去(页380)。
绵羊们的角色并非总是被动的。动物农场的粮食开始发生短缺,饲料定量急剧减少,动物们只能吃到谷糠和甜菜。为了不能让外部获知这个事实,绵羊们受命在温佩尔(动物与人类的中间人)能够听得到的距离,乐观而欣喜地议论动物农场粮食大幅增加的消息(页354),从而借其传播动物农场繁荣昌盛的虚假信息。被利用的绵羊们似乎感到被重用,把发布欺骗信息当成神圣使命,竟然洋洋得意。
当动物主义的指导思想遭到背弃,动物主义的七戒遭到篡改,《英格兰牲畜之歌》遭到禁止,甚至其统治者——猪集团竟然模仿人类直立行走,绵羊们再这么盲目乱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显然不合时宜。不过,教会这些愚昧的动物并不容易。尖嗓开始对这些绵羊进行封闭培训和系统教育,并不无困难地对它们重新洗脑(页391),教会它们传唱一首新的歌曲。这帮愚昧、盲从的动物,既不懂其中的道理,也不顾内中的逻辑,更不管与一贯的唱法是否矛盾和对立,它们只顾鹦鹉学舌,猪云亦云,唱起来仍然是那么集体无意识——“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它们似乎决心把盲从进行到底。而此时的“动物农场”,不仅仅在名义上,早已倒退回“庄园农场”时期。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