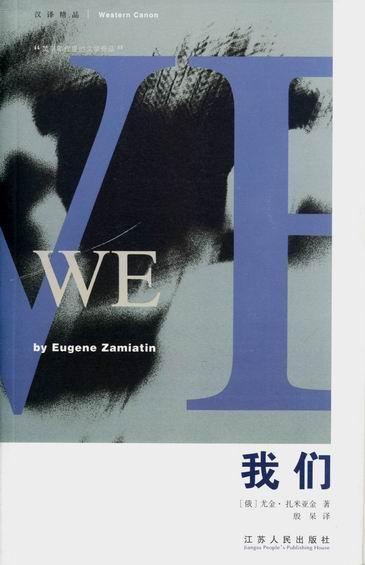
《我们》(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部小说,作者是俄国的尤金·扎米亚金。
20世纪有三部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从出版时间算起,《我们》(1924年)应是开先河者。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美世界》(1932年)、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其创作灵感都有《我们》的痕迹。
扎米亚金原本是造船工程师,却因爱好写作而出名。他一生经历了沙皇与俄共两个时期。这位以讽刺文学见长的作家,当《我们》在国外出版的消息传到国内,无法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1931年6月,被迫上书斯大林请求出国,其理由是,“失去写作的权利,不啻于被判处死刑”。经高尔基斡旋,扎米亚金的愿望得以实现。移民法国后,政治控制是消除了,创作源泉却丧失了,1937年客死巴黎。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非针对俄共政权。该书创作于1920年,适值俄共建政之初。其在国外出版时,列宁刚刚逝世不久。从时间推断,此时俄共的体制弊端尚未充分暴露,书中的情节与思想完全属于作者自己的理性思考与文学塑造,并不具有影射俄共政权的性质。
据《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介绍,《我们》描写的是26世纪的联众国。这个国家以一道绿墙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桃花源,但又比桃花源充满现代气息。在“没有幸福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幸福”的单项选择中,这个国家选择的是后者,即奉行“没有自由的幸福”原则。作者生活的年代还没有电视监控系统,小说中的人物全部生活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随时受到“安全卫士”(秘密警察)的监视。这些玻璃房子具有透明的四壁,宛如由空气编织而成。“每个人都生活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无时不刻沐浴在光线中。我们彼此之间赤诚相见,毫无遮掩可言。”人们自嘲说:“我的家是我的堡垒!”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我的家是我的监狱!”
这个国家的居民没有名字,只有号码。D-503是男主人公,I-330是女主人公。书中的人物还有胖女人O-90,诗人S-4711,黑人R-13等等。号码们都要严格按照时间表作息,同时起床,同时工作,同时进食,同时睡眠,同时醒来。号码们统一着蓝色制服,胸前统一佩戴号码。即使行进在大街上,也要四人一排,步伐整齐。在联众国里,号码们连思维也一模一样,“这是因为已经没有哪个人是个体,我们都是整体中的一员的缘故。”号码们并非完全没有“自由”,只有在“私人小时”,才被允许拉下窗帘。号码们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根据联众国《性法》,只有经过批准,只有在性日,一个号码才能与异性号码进行交媾。即使如此,也必须事先到实验室测试荷尔蒙,并领取粉红色的票据。
联众国最高的、唯一的领袖是无所不能者,从其名字可知,他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了。在一些国家,最高领袖被称为“红太阳”或“金太阳”,但在D-503眼里,最高领袖却是一个“睿智的白蜘蛛”。他这样描述他对无所不能者的无限深情,“是他,从天而降,……成百万颗心一齐向他扑去。……从高空俯瞰一切:一圈圈同心圆形状的座位,上面点缀着蓝色制服(指号码们)组成的一条条长线——宛如一个点缀着无数微型太阳的(闪闪发亮的证章)的大蜘蛛网。圈子中央是睿智的白色蜘蛛的位置……无所不能者身着白衣,睿智地将我们的手脚束缚在有益的幸福之网中”。号码们对无所不能者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联众国的天空响彻着《向无所不能者的每日颂歌》。
无所不能者对于国家的治理,有两项法宝,一是死刑机(无所不能者只要按下电钮,进入死刑机的号码们,就会变成一缕青烟),一是气钟罩(号码们进入其中,气体被慢慢抽出,号码们结束生命的过程十分安详)。在联众国,“国家(人道主义)禁止对个人谋杀,但它并不禁止对成百万人进行缓慢、逐步的谋杀。”号码们对于无所不能者永远“没有疑虑”,因为他“永无错误”。无所不能者的意志如同乘法表一样,“只存在一个真理,通往它的道路也只有一条,这真理就是四;这道路就是二乘二。”
单个的号码——“我”,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号码的集合——“我们”。在联众国,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我”与“我们”的关系。在“我”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天平:“一边摆的是一克,另一边摆的却是一吨;一边是‘我’,另一边是‘我们’,即‘联众国’。……在国家面前,要说我有任何‘权利’,这简直就像在断言一克在天平上可以与一吨抗衡!合乎情理的分配应该是这样的:‘权利’由吨享用,‘义务’让‘克’承担。想要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伟大,最自然而然的办法就是忘记一人是一克,而是要牢记一个人只是一吨的100万分之一!”
正因如此,联众国的“积分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时,发射台上的12个“号码”在喷射管的火焰中,“只剩下一点残屑和焦灰”,然而,这“丝毫不曾影响我们的工作节奏”,“区区12个‘号码’连联众国人口的10亿分之一都不到。实事求是地讲,这不过是个第三级的‘无限小’罢了。”虽然我们是“一个有着百万头颅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分子、原子和细胞一样,心中涌动着谦逊的欢乐。……(号码)们知道‘羊群的教会’的伟大意义。他们知道顺从是美德,骄傲是邪恶;‘我们’源自上帝,‘我’源自魔鬼。”
联众国最重大的节日是“一致日”。一致日就是无所不能者的年度选举日。无所不能者已经连续47年全票当选。“明天,我们会再次将我们坚固无比的幸福堡垒的钥匙交给无所不能者。”D-503为联众国井井有条的选举组织工作感到自豪——“任何意料之外的事件都不可能发生”;号码们最自豪的是能够提前知道选举结果——“选举本身具有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选举过程并非想像的那样顺利,在听到“反对的请举手”后,按惯例,“所有人都将一动不动地坐着,在这个众号码之王提供的有益枷锁下快乐地低垂着脑袋。”这次不同了,竟然有成千上万只号码举起了反对的手臂。接下来的情节是可以想像的,“安全卫士慌张的身影狼奔豕突”,无数个号码惊恐地骚动。然而,次日的《联众国报》却报道,“大家翘首以待多时的一致日庆祝活动于昨天举行。曾无数次证明他的无上智慧不可动摇的无所不能者获得一致通过,连续第48次全票当选。”
那成千上万的反对者,因在“一致日”里表达了“不一致”,而成为“幸福的敌人”,他们的选票全部作废(原本就没有选票,只是白白举起了手臂),同时不再承认他们作为联众国的基石。在全部得票中,扣除全部的“非赞成票”,无所不能者再度全票当选。这样做当然是有理由的,这些反对者如同“闯进音乐厅的病人的几声咳嗽”,自然不能被“视为一场伟大交响乐的一部分……”
联众国并非处处阳光灿烂,澄彻透明,在严密控制的罅隙里,也会孳生细菌,出现“魔非”(魔非斯特,魔鬼)。D-503就成了这样的细菌,他作为 “积分号”宇宙飞船的制造者,本来是联众国的优秀公民,由于他体内残存的人性与本能,他不仅与I-330频繁幽会,还使O-90怀上了身孕。他不知道,I-330是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从而成为其“和平演变”的牺牲品。已经上了贼船的他坦诚,“我再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有条不紊地吞噬着细菌……的啮菌细胞;显然,我自己也是一个细菌。”
他们密谋策划的驾驶“积分号”宇宙飞船冲出绿墙的叛逃计划败露之后,他被认定“有病了”,他患的是“幻想症”。联众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并提出建议,“幻想源自一个中心——一团可怕的神经结,它位于大脑的前突部位。用 X光对这团神经结进行三步治疗,你们的幻想症就可以治愈!”
D-503观察了一些作过手术的号码们,治疗效果比洗脑更胜一筹,“他们不是人,只是一种有点像人的机器。”他们高举一面白色旗帜,上面绣着一轮金太阳,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我们是第一批!我们已经作了手术!你们所有人,快跟着来吧!”只是,这些字如果译成中文,不知应当如何翻译。
然而,是否进行脑部手术,并不取决于号码们的自愿。《联众国报》的大字标题警示:“明天,一切工作都必须停止,所有号码都必须作手术。不作手术的人将被送上无所不能者的死刑机。”安全卫士把D-503捆在桌子上,进行了伟大的手术。奇迹出现了,第二天,当他出现在无所不能者面前时,所有的人性完全消失,如同一个被无所不能者遥控的电动玩具,不仅坦白了他们的叛逃经历,并为成为“幸福的敌人”悔恨不已。即使如此,D-503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以前我始终难以做到这一点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我病了——灵魂病。”然而,I-330——那位远比D-503坚强的号码及其同伙,她(他)们全部被投入了无所不能者的死刑机。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