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无法成为权力监督的政治基础
安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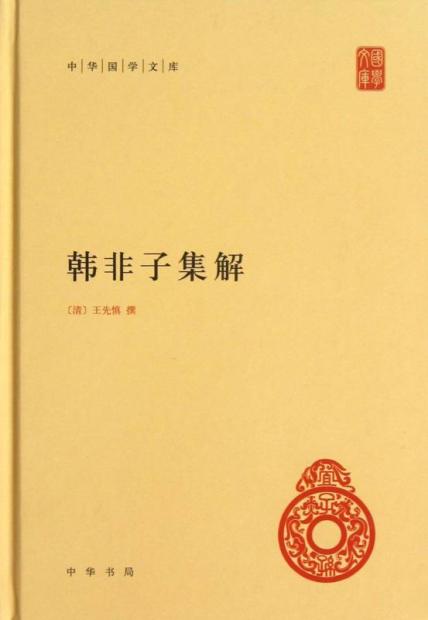
本届领导集体三年施政一大亮点,就是突出了“依法治国”,其标志就是中央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的决议。依法治国的精髓在法治,从而与人治相对立。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之初即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加强权力监督。
在我国,有一批由民脂民膏豢养的“特别”学者,中央每一决策出台,这些人物纷纷粉墨登场,摇唇鼓舌,歪解胡说。此次,他们居然把“依法治国”与韩非子连在一起,称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云云。真不知这是对“依法治国”的推崇还是贬低?

人们知道,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不仅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而且是君主专制之大师。他为专制君主设计的“法、术、势”的独裁理论,与意大利专门教君主作恶的马基雅维里如出一辙。韩非子可谓中国的马基雅维里,《韩非子》可谓中国的《君主论》。韩非子确实说过:“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P31)并曾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然而,他所说的“以法治国”,与今天所说的“依法治国”,“依法”还是“以法”,虽只一字之差,在英文里却有着本质区别。“依法”之“法治”即“Rule of law”,意味着法律高于一切,实质是国家应该由法律来统治,而不是由政府官员个人意志来决定。“以法”之法治即“Rule by law”,意味着法律是政府的工具,实质是政府用法律施行其统治、推行其决策。韩非子讲究实用,他坦率指出:“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同上)法律不过是一种举措、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已。
在我国,从古到今,都有那么一些无良文人,专门为权势者出谋划策,其中大多是馊主意与坏主意。这类人物,儒家以孔子为代表。鲁迅曾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329)法家则以韩非子为代表,而在厚黑方面比之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韩非子作为一个失势的贵公子,为韩国的衰败而焦急,他以亲身体会告诫君主们,以一人治天下,无论如何劳心费神,即使耗尽视力、听力和脑力,也无法应付臣下的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原文是这样的:“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韩非子集解》,P36)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同上书,P115)这些意思说白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君主不可信任臣下”,这可称为君专制的“韩氏定理”。为证明这一定理的普世原则,他专门举了李兑饿死主父(赵武灵王),郦姬杀害申生的例子,以此警告君主,“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同上)妻子儿女都不应信任,何况他人!
韩非子为专制君主所出之谋、所划之策,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当今世界,君主政体、皇权政体以及形名不同而实质相同的独裁专制体系,在历史潮流的冲刷下,已灰飞烟灭,所剩无几。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当家作主,人民主权,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的标志事件之一,就是北美殖民地挣脱宗主国的压迫,通过革命与战争而建立现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相区别)。参加建国事业的人们公开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以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巩固这些权利,在人们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并成立新的政府,……”(《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P49、50)在这种政体中,没有了君主,没有了贵族,韩非子关于君主不可信任臣下的告诫当然也已过时。
这是一种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之下,奉天承运,君权神授,真龙天子,皇位世袭,都不存在了,君主对臣下的信任不复存在,民众对权力的信任成了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最高指示。在这个句式里,将群众排在信任序列的前排,相对于人民主权尽管打了折扣,毕竟也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人类具有返祖或复古的习性,尽管资本主义复辟的警告耳提面命,复辟一个不曾存在过的社会总是有些虚无。两千多年的专制幽灵聚而不散,终于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发生了长达十年的封建专制复辟,以至于出现了韩非子的逆定理,虽然“君主不可信任臣下”,而“臣下必须信任君主”,不仅如此,还要变本加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由于当年否定“文革”不彻底,至今余绪犹存,今天一些人似乎不喊什么人“万岁”就无所适从,似乎不挂什么画像就六神无主。
阿克顿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P342)也是一条定理。在它面前,不承认任何权力具有拒腐蚀、永不沾的定力,不承认任何权力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天性。在它面前,任何权力都不具有伟大、神圣、英明的性质,相反,所有权力都具有腐败、堕落、变质的趋势。说实话,我们也希望将权力视为“天使”,然而,“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P264)我们不希望将权力视为“无赖”,然而,“夸耀任何政府体制的优越性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P27)历史证明,如果从天使的角度去信任权力,只能纵容权力的肆虐与堕落;只有从无赖的角度去防范权力,才能防止权力的腐败与变质。
空谈信任显然无益于权力监督。“只有权力才能抵制权力,一种倾向只能用另一种倾向进行抵制。”(《卡尔霍恩文集》<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P12)在当代政治文明史上已然成为共识。这一思想,不仅出于启蒙时代法国的孟德斯鸠,也出于建国时代美国的卡尔霍恩。“实施权力之人和服从权力之人,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间乃针锋相对的关系。”(同上)针锋相对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监督者与反监督者的对立。任何权力都不会心甘情愿地被关进笼子。在这里,需要的不是什么政治信任,需要的是设计制度笼子的宪法智慧。由于“人类本性的构造,使得统治者倾向于压制被统治者,而对政府自身的目的无所顾忌;……”(同上)因此,应当强调的是对权力的警惕,而非对于权力的信任。《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更加明确地指出:“如果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何况有些权势者并非我们的真实选择——作者),认为他会保障我们的权利,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幻想:那个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专制之母——自由政府是建立在警惕而不是建立在信赖上面。是警惕而不是信赖,规定了限制权力的宪法,以制约那些我们不得不托付权力的人;……所以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信赖人,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制约他不做坏事。”(《杰克逊集》,三联书店,1993年,P487、488)
当权力不再是凌驾社会之上的君主,当权力已成为服务民众的公仆,那么,就不再是君主是否信任臣下,政府是否信任民众(至少不能随时把民众当成“不安定因素”)的问题,而是人民不能一厢情愿地信任政府。现代意义的政府如同物业公司与家政保姆,为防止政府的越权与滥权,民众作为社会的主人,只应以挑剔的、不信任的眼光去监督政府,以防止这个社会公仆的监守自盗与偷懒耍滑。我国宪法虽然明文昭著,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然而,人们司空见惯的却是权力的跋扈、腐败、淫荡、奢靡,以致贪污横行、小三成群、血火强拆、暴力截访、徇私枉法……在我国,不是民众对政府是否信任的问题,而是人们不敢不相信政府。的确,由于“中国特色”的不同国情,中外之间的确没有多少可比性。
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没有榜样”,当代中国不仅失去了学习先进国家的积极性,而且产生了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的大国冲动。遥想1980年代,总结苏联肃反教训,反思我国文革教训,毛泽东、邓小平的结论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英美国家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同苏联崇拜斯大林,我国迷信毛泽东,何止是信任?四个无限(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才是基本要求。在专制权力面前,人们丧失了思考能力、判断能力、监督能力,人们不仅噤若寒蝉,而且助纣为虐。正是出于对于权力的信赖与恐惧,人们才会主动上缴头颅,束手待毙。近年来,再度涌现出一股“表态热”,地处边鄙的云南,狠批“吃饭砸锅”,天子脚下的河北,严禁“妄议中央”。在他们看来,此种行径都表现为缺乏对权力的高度信赖,未能从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然而,盲目的、无条件的信赖,其实并不符合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行为要求:“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P827)毛泽东针对的是“任何事情”,这显然是一个全称判断。一些极力为毛泽东文过饰非的人物,其实并不真想全面接受已经实践证明的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确部分。
将“依法治国”导入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歧途,已经引起世界舆论的注意。《金融时报》中文网2015年8月19日有一篇《透视中国领导人的“法治观”》,对于这种法治提出了质疑。一些愚蠢的御用学者的愚蠢行为,不仅在国际上对中国形象平添了不良观感,而且从客观上削弱了人们对于权力本来不太牢靠的信赖。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