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晚年谈了些什么?
安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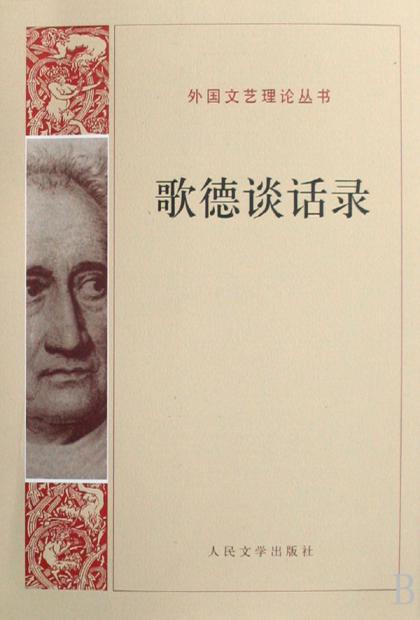
我曾两度邂逅法兰克福,一次是在2003年4月,在法兰克福机场中转去巴西圣保罗,未曾迈出机场一步,并不算真正到达这座城市。另一次是2009年6月,到法兰克福访问,曾在罗马广场逗留,曾在欧洲银行留影,也曾在美因河畔漫步。由于当时的关注点不在文化古迹,竟未留意,这里就是世界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歌德的故乡。
近日读《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作者是歌德的粉丝爱克曼。在歌德生命的最后九年,爱克曼担任歌德的助手或秘书。在与歌德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话题非常广泛,广泛的程度竟然成为一本长达288页(包括附录)的名著。这些谈话,有背景、有情节,涉及诸多领域。在一篇介绍性的文字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就几个问题作点简述。
“现在制度的朋友”
1824年2月4日。歌德不无抱怨地说,“我既然厌恨革命,人家就把我叫做‘现在制度的朋友’。这是一个意义含糊的头衔,请恕我不接受。现存制度如果贤明公正,我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现存制度如果既有很多好处,又有很多坏处,还是不公正、不完善的,一个‘现在制度的朋友’,就简直无异于‘陈旧腐朽制度的朋友’了。”(《歌德谈话录》,P24)
歌德在这里阐述的是作家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一个作家在一般意义上、或者无条件地成为“现在制度的朋友”,当然是可悲的。在现代历史上,有鲁迅式的作家,有浩然式的作家。在政治权力面前,作家应当有自己的价值、自己的选择,这种价值、选择并非完全个人式的,而是人类的、世界的、时代的、人民的。偏离这样的坐标点,一味追求做“现在制度的朋友”,等于在奴才与犬儒之间作出选择,其所追求的不再是真理、正义与良心,而是权力、金钱与名誉,从而成为“无脊椎动物”。
不过,歌德的自我辩解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同上,P24)
歌德这个观念让我想起中国古代文人金圣叹在评论《水浒传》一书时的名言:“乱自上作”。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往往先有乱政才有乱民,先有刁官后有刁民。正如歌德借用剧中人物之口所说的:“下层阶级的革命暴动都是上层阶级不公正行为造成的后果。”(同上,P23)文人作为公民一分子,在现代社会中,负有监督权力和政府,弘扬正义与公平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与权力和政府合作,在权力和政府遵守法律时似乎没有什么,如果权力和政府逾越法律的牢笼,肆虐社会,危害公众,文人此时与权力与政府合作,几乎等于投怀送抱或为虎作伥。
“君主的一个仆役”
1825年4月27日。歌德有点激愤地说,“现在还有人说我是君主的一个仆役、一个奴隶。好象这种话有什么意思似的!”(《歌德谈话录》,P83)他反问道:“我所服役的是一个暴君?一个独裁者?是一个吸吮人民的血汗来供他个人享乐的君主?”(同上)他在对魏玛大公爵进行了大量辩护之后指出,“如果我被迫当一个君主的仆役,我至少有一点可以自慰,那就是,我只是替一个自己也是替公共利益当仆役的主子当仆役罢了。”(同上)在他眼里,他这位主子是一位“替公共利益当仆役”的“人民公仆”,而充当“人民公仆”的仆役,不仅不应受到谴责,而且感到自慰。
臣服于、效忠于一个暴君、一个独裁者是不好的,臣服于一个明君、一个英主,是无可厚非的。在这一点上,歌德与他前后一百年里欧洲大陆的思想家比起来,的确是一个矮子。与他同时代的杰斐逊,不仅投入到建立美国共和制度的理论、舆论准备,而且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度的诞生。其实,美国的共和制度,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也是欧洲思想家两个多世纪的思想启蒙的必然结果。这里面不仅有英国学者洛克的政府理论(《政府论》),也有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法治思想(《论法的精神》)。这两位几乎比歌德早出生一个世纪的哲人,其思想的光辉竟然没有丝毫照进歌德的心田里。
相比之下,歌德的眼界与水平实在差得太远。歌德的思想让人想起早年的开明专制,想起人们常说的“好皇帝”,想到近年的新权威主义。这种理想模式其实早在一百年前的英国就已经出现过。英国学者密尔曾经提到过一句英国谚语:“假使能保证有一个好的专制君主,君主专制政体就会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P34)那么,好的专制政府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政府里,就依靠专制君主来说,不存在国家官吏的实际压迫,但人民的一切集体利益由政府代他们进行管理,有关集体利益的一切考虑由政府替他们去作,他们的思想形成于并同意于这种对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放弃。一切事听任政府,就象听任上帝一样,意味着对一切事毫不关心,并把它们的结果,如不合自己的意思,当作上天的惩罚加以接受。……整个人民的才智和感情让位给物质的利益,并且当有了物质利益时让位给私生活的娱乐和装饰。”(同上,P37)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民至多如同绿色食品生产基地饲养的“幸福猪”,而专制君主则是这个饲养场的场主。由此可见,“好的专制政治完全是一种虚假的理想,它实际上(除了作为某种暂时目的的手段)是最无意义和最危险的奇异想法。以毒攻毒,在一个文明有所发展的国度,好的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同上,P40)由此可见,密尔如同巨人,歌德如同侏儒;密尔是民众权利的卫士,而歌德则是一个可怜的臣仆。
“多余的自由有什么用”?
1827年1月18日。在谈到席勒的作品时,歌德说,“自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多余的自由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会用它?”(《歌德谈话录》,P109)“一个人如果只要有足够的自由来过健康的生活,进行他本行的工作,这就够了。……市民和贵族都一样自由,只要他遵守上帝给他的出身地位所规定的那个界限。贵族也和国王一样自由,他在宫廷上只要遵守某些礼仪,就可以自觉是国王的同僚(或:和国王平等)。自由不在于不承认任何比我们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来比我们高的人物。因为尊敬,我们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认他,我们就表明了自己心胸中有高贵的品质,配得上和高贵人物平等。”(同上)
歌德所说的自由,与英国学者密尔所说的社会自由与公民自由大体同义。密尔曾对自由下过一个定义,“所谓自由是对政治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P1)如同阿克顿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样,“统治者必然处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相敌对的地位。”(同上)也是一条政治定律。“无论如何,他们之握持权威绝不视被管治者高兴与否;人们对其至尊无上的地位从不敢有所争议,或许竟不想有所争议,不论会采取什么方策来预防其压迫性的运用,他们的权力被看作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同上,P1-2)
然而,歌德先生不但不担心自由被剥夺、被侵犯,还担心自由多了不知怎么用。在他看来,农民有种地的自由,渔夫有打鱼的自由,猎户有打猎的自由,商贩有经商的自由,官员有当官的自由,国王有治国的自由,他们的自由都是一样的、等值的,而且各得其所。唯一的条件是“遵守上帝给他的出身地位所规定的那个界限”。他却不知道,这些社会角色一旦不遵守这些界限会怎样?当然,他的确不知道梁山泊的渔民会碰到官府勒索,登州的猎户会遇到毛太公贪占猎物。他也从来没有遇到农民种地会被割“尾巴”,商贩经营会碰到“城管”,甚至足不出户的良民也会遇到“强拆”。歌德的自由理论极像中国的孔夫子,只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安于本分,与世无争,只能忍气吞声,决不犯上作乱,从而建立起一个和谐世界。然而,歌德又不同于孔夫子,他以为只要自己尊敬地位高的人物,比如贵族和国王,自己的心灵与感觉就能与贵族、国王比肩而立,而这是非典型性的中国心理——“阿Q主义”。
“中国人几乎与我们一样”
1827年1月31日。歌德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谈话录》,P112)“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同上)“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同上)歌德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描写是非常诗意的,中国人几乎生活在外国的伊甸园或中国的桃花源里,他的笔触一定会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欣慰。首先他对中国的了解都是间接的、肤浅的,通过早年传教士的一些不确切的材料得出的不确实的印象。其次,他完全忽略了一个东方古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极其不同的国家。
比歌德这次谈话早了30多年,即1793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访华团,第一次直接地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访问和考察。使团成员马罗就访华印象写道:“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P346)马戛尔尼的结论是:“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同上)
与歌德同时代的哲学家黑格尔,根据欧洲人对中国考察的第一手材料,他得出结论,中国还处于“历史的幼年时期”,只是一个“可以称为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这部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P107-109)“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指皇帝),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它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它自己。”(同上,P108)“在中国那个国家里,皇帝的道德意志便是法律:但是这样一来,主观的、内在的自由便被压抑下去,‘自由的法律’只能从个人外界方面管理他们。”(同上,P159)
许多年过去了,中国从满清到民国,再到今日中国,国人骨子里的观念到底变了多少?中国变化的只是政体的形式,国体据说是变了的,但变化的只是其外壳,制度的理念、权力的规则、掌权的方式,其实一点也没变。然而,这些都是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而言的。即就歌德赞赏的中国男女道德而论,他肯定没想到在今日中国,在两性道德上,最放纵、最淫荡的竟是各级官员,以至于“二奶”成群,“小三”结队,而在长期以来,“以吏为师”的古老中国,这样的示范,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牛顿的错误
1827年2月1日。歌德曾经论证牛顿光和颜色的理论是个错误,当谈到某些教授仍在讲解牛顿的学说时,歌德说,“这并不足为奇,那批人坚持错误,因为他们依靠错误来维持生活,否则他们要重新从头学起,那就很不方便。”(《歌德谈话录》,P117)爱尔曼说,“但是他们的实验怎么能证明真理,既然他们的学说的基础就是错误的?”歌德说,“他们本来不是在证明真理,他们也没有这种意图,他们唯一的意图是要证明自己的意见。因此,他们把凡是可证明真理,证明他们的学说靠不住的实验结果都隐瞒起来了。”(同上)
歌德谈到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一些已经实践证明了的落伍于时代、脱离了实际的理论,一些学者仍然当作老奶奶箱底的宝贝,不时拿出来晾晒,不时拿出来炫耀。不要以为他们只是虔诚地“坚持错误”,其实“他们依靠错误来维持生活”,也是非常现实的考虑。一些人一生中只接受了这些陈腐的理论,而他们对于新起的理论,要么思想僵化不肯接受,要么头脑迟钝学不进去,要么感到风头一变仍有销路,这些陈腐的理论,即使当不成“通灵宝玉”,也要当作“吃饭家什”,因为他们除了这一“薄技”在身,身无长物,只能将这些老货色花样翻新,炒来炒去。歌德说这些人目的在于“维持生活”,可谓一语中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重新从头学起”,把旧货“货与帝王家”,是因为“帝王家”仍有不此之需。至于说他们长篇大论,连篇累牍,喧天鼓吹,是否能“证明真理”,歌德的看法我是同意的,“他们本来不是在证明真理”,而是为了献媚邀宠。为了生计,他们不仅没有证明真理的意图,更没有证明真理的能力,他们所要证明的,只是陈腐的旧货仍有价值,他们仍是这些旧货的拥有者与欣赏者,他们还不是僵尸,他们还有一口气,他们还有残存的价值。为了证明他们的旧货奇货可居,甚至把近年来新发现的证明这些旧货已经陈腐的证据——事实与真相,证明时代已经进步的新见——理论与学术,像歌德所说的那样统统“隐瞒起来”,以免失去了早已枯萎了的市场。正因如此,我赞成歌德的意见,“我们对于真理必须经常反复地说,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并且不是有个别的人而是有大批的人宣传。在报刊上,辞典里,在中学里,大学里,错误到处流行,站在错误一边的是明确的多数。”(同上,P178)
辩证法
1827年10月18日。黑格尔来访,三句话不离本行,“辩证法不过是每个人所固有的矛盾精神经过规律化和系统化而发展出来的。这种辩证才能在辨别真伪时起着巨大的作用。”(《歌德谈话录》,P162)歌德插嘴说,“但愿这种伶巧的辩证技艺没有经常被人误用来把真说成伪,把伪说成真!”黑格尔说,“你说的那种情况当然也会发生,但也只限于精神病患者。”(同上)
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体,前者的版权属于费尔巴哈,后者版权属于黑格尔,马克思把二者杂交形成了唯物辩证法。在成为我国指导思想之后,前30年基本上虚无缥缈,整天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整天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物质刺激,整天物质出精神,精神变物质,搞得物质极度贫乏,精神不能当饭吃,害得全国人民食不裹腹,整天饿肚皮。30年河东30年河西,后30年,走向另一极,中国竟然成了一个“唯物”、“唯钱”、“无德”、“无良”的世界,官方追求的是GDP,民众追逐的是人民币,以致山岭破碎、江河污染、雾霾罩地、毒气熏天。举凡地沟油、毒奶粉、苏丹红、激素鱼……整个民族易粪而食,互相伤害。正当人们为这些唯“物”论的恶果忧心忡忡之际,辩证法出来了——大家不要着急,不要上火,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坏事总会变成好事。过去只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有辩证法能把坏说成好,把假说成真,把恶说成善,把丑说成美。不过,人们并不是故意的,而是如同歌德所说,“经常被人误用”而已。比如,雾霾是对付美军激光武器的利器,毒奶可以把人民团结在一起。三年灾荒饿死几千万人是坏事,但我们缴了学费,受了教育,变得聪明,促进了发展;“文革”十年浩劫是坏事,但我们经历了挫折,实行了转变,才有了改革开放。“坏事变好事”,掩盖了坏事的根源,淡化了坏事的危害,逃避了坏事的责任。以致于不思悔改、无视教训,从而为坏事再次出现埋下了祸根,而坏事的始作俑者永远逍遥法外。黑格尔虽然并不否认“那种情况当然也会发生”,然而,那些人绝对不是“精神病患者”,而是一个个头顶光环的人精。
先个人后社会
1830年10月20日。歌德指出,“我却认为每个人应该先从他自己开始,先获得他自己的幸福,这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幸福。我看圣西门派的学说是不实际的、行不通的。因为它违反了自然(人性),也违反了一切经验和数千年来的整个历史进程。如果每个人只作为个人而尽他的职责,在他本人那一行业里表现得既正直而又能干胜任,社会整体的幸福当然就随之而来了。(《歌德谈话录》,P224)
圣西门被定性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果说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祖根之一,那么圣西门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祖根之一。有人说社会主义是从空想到科学,实践中社会主义却是从空想到空想。圣西门的幸福观强调先社会、后个人,个人服从社会,倒是得到了传承。在中国的古代智慧中,向来强调:“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谏逐客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荀子·劝学》)这其中强调的都是积少成多、积微成著,其中贯穿的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然而,从圣西门开始,荒唐的逻辑即充斥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正如歌德所说,“每个人应该先从他自己开始,先获得他自己的幸福,这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幸福。”在“文革”前的30年中,以建设社会主义天堂为名,以集体主义的手段,通过剪刀差等政策,长期地、大规模地掠夺农村和农民,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差别,而且几乎摧毁了农村生产力。改革开放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只不过将种地的权利还给了农民,农民就很快实现了温饱。在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只因放弃了以全面发展、顾全大局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与发展,迅速爆发的社会生产力,短短几年竟然使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而这在“文革”中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在那个荒唐的岁月中,先治坡、后治窝;先大家,后小家;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些荒唐的逻辑,“因为它违反了自然(人性),也违反了一切经验和数千年来的整个历史进程”,而遭到时代的唾弃。然而,在“文革”前30年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似乎对此情有独钟,看来在观念领域,清除过去岁月的极“左”宣传遗留的痕迹并不容易,尽管这种宣传背离中国古训,违背马列主义!
“什么叫做爱国”?
1832年3月,歌德去世前几天,他这样说,“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诗人会爱他的祖国;但他在其中发挥诗的才能和效用的祖国,却是不限于某个特殊地区或国度的那种善、高尚和美。无论在哪里遇到这种品质,他都要把它们先掌握住,然后描绘出来。他象一只凌空巡视全境的老鹰,见野兔就抓,不管野兔奔跑的地方是普鲁士还是萨克森。”(《歌德谈话录》,P259)“什么叫做爱国,什么才是爱国行动呢?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有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此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吗?还有比这更好的爱国行动吗?”(同上,P259)
歌德这段关于爱国主义的谈话,涉及两个问题,作为诗人和作家,他当然是爱国的,爱的正是自己国家的“那种善、高尚和美”,而“善、高尚和美”又不仅仅局限于国界之内。因此,歌德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诗人、作家甚至公民,应有博大的胸怀,应有人类之爱,凡是能体现“善、高尚和美”的事物都在爱的范围,都应成为诗人、作家笔下的素材,“他象一只凌空巡视全境的老鹰,见野兔就抓,不管野兔奔跑的地方是普鲁士还是萨克森。”这当然是个形象化的说法。爱国主义不能成为狭隘的感情与行为,敌国的事物再好也要抨击;本国的事物再坏也要辩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都不是健康的爱国主义。对于体现人类之“善、高尚和美”的赞美与歌颂,将会受到全人类的尊敬。
不过,爱国主义也不是一味地赞美与歌颂,赞美其应当赞美者,歌颂其应当歌颂者,自然是正确的。然而,爱国也需要“斗争”与“排斥”,即歌德所说的“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正如一句法国名言所说,“假如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一个国家如同一个巨大的森林,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中,既有高大的乔木,也有丛生的灌木;既有食肉动物,也有食草动物;既有歌喉婉转的黄莺,也有啄食害虫的啄木鸟。没有哪个国家不存在歌德所说的“有害的偏见”与“狭隘的观点”,甚至存在着巨奸大恶。如果以爱国主义为名,否定“斗争”与“排斥”,无疑于维系一个只有乔木、没有灌木,只有益虫、没有害虫,只有黄莺、没有啄木鸟的生态系统。
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记录了歌德生前最后几年关于、文化、美学、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言论及行动,译者认为,《歌德谈话录》是研究歌德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在文艺方面,它记录了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然而,同为德国人,比歌德稍晚的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也是值得注意的。恩格斯认为,歌德具有“伟大的诗人”与“德国庸俗市民”的两面性,“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P256)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歌德,经历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占领德国等重大事件,动荡年代产生的伟大作家,既充分展现了高度才华,也充分体现了其复杂的一面。阅读这部作品,不能对其所涉猎的广泛领域发表意见,只就其中产生兴趣的话题,作点记述与评论。
下面是“安立志”的文史平台。让我们大家一起读史、品书、论事。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