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的眼光”
文 \ 安立志
朋友发我一条微信称,杂文圈最近冒出一种声音——有人以今天的眼光看鲁迅,揪住鲁迅的小辫子不放。这话的口气居高临下,似乎在为杂文界立规矩——鲁迅不许质疑与批评。

不许“以今天的眼光看鲁迅”,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其实质就是不许“以今天的眼光看历史”。怎么理解这个“以今天的眼光”呢?
李大钊曾有一篇名文,标题就是《今》,他指出:“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现在”就是“今”,“今”就是现在。没有了“今”,不仅中断了“过去”,也阻断了“未来”。不许“以今天的眼光看历史”,是不是李大钊批评的“厌今派”,“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192)至少对鲁迅的评价,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由“以今天的眼光”想到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2)。有学者指出,“历史是在‘现实关怀’引导下复活于当前的过去,现实则是经由过去熏染而具有历史内涵的当前存在。”(2016年8月19日《文汇报》)今天是历史的延续,今天也是未来的历史。看待历史事件或人物,古人有古人的价值标准和审美体系,今人有今人的价值标准和审美体系。今天无法观照未来,预言家与算命师往往鱼龙混杂;今天可以回望过去,无人回顾的历史岂不都是尘埃。王羲之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诗序》),着眼点也是“以今天的眼光”。“以今天的眼光看历史”与“以当时的眼光看当时”,具有完全不同的时空维度,前者可以看到时代的局限和进步,后者看到的只是黑格尔式的“存在即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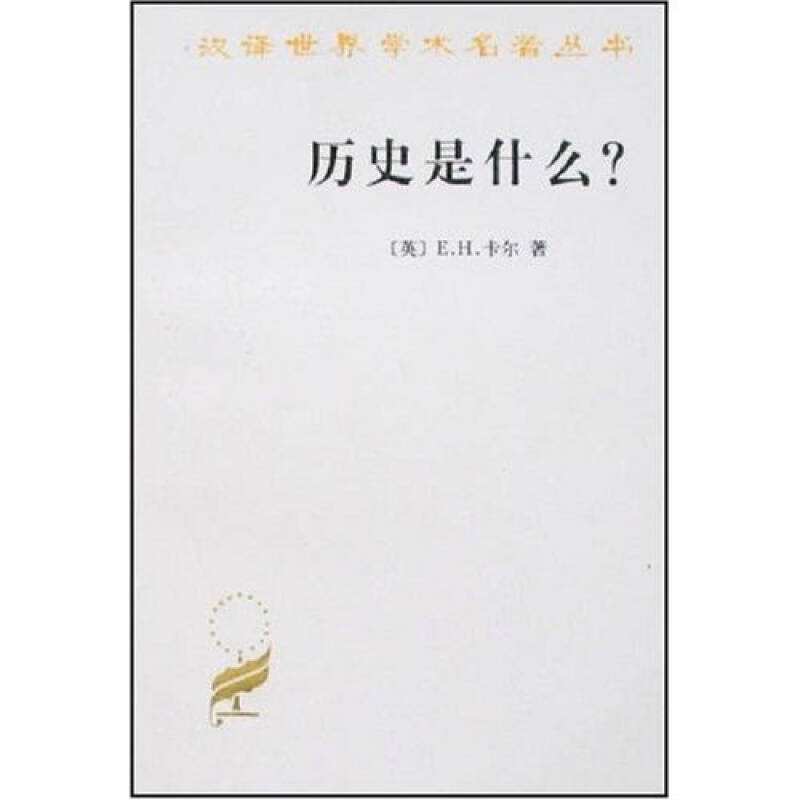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指出:“我们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页109)岂止如此,以当时的眼光来品鉴,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皇权、留辫曾经是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纳妾、裹脚也曾是传统悠久的民间习俗。“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皇权、留辫已然成为历史的尘埃,纳妾、裹脚则已沦为民族的耻辱。近代以来,正是由于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追赶时代潮流,正视民族弊端,敢于“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历史,考问历史,反思历史,才逐步地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地球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又冒出一股反对“以今天的眼光看历史”的论调,使人们真切地感觉到鲁迅同代人曾经抨击过的守旧思潮又卷土重来。
如何看待历史遗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今天的眼光”与“当时的眼光”区别在哪里?不妨试举几例。

如何看待历史遗迹?即以长城为例,当时的眼光与今天的眼光迥然不同。查不到秦人对长城的评论,可以想像,在当时人的眼里,秦始皇建造万里长城,肯定是“帝国工程”、“国防大计”。当时的人们尚未从“秦王扫六合”的辉煌中冷却下来,王朝却伴着“金棺葬寒灰”迅速崩溃,从而失去了有关长城的原始记载。作为参照,西汉的贾谊去秦不远,著名的《过秦论》,即使是批评,也留下了对长城的赞誉,“及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2)鲁迅对长城的看法,与贾谊远隔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显然属于“今天的眼光”。鲁迅认为,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61)在鲁迅看来,作为防御工程,长城毫无作用。不仅如此,长城甚至是封闭保守的象征,他以讽刺的口吻写道:“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同上)
如何看待历史事件?可以“文革”为例。按照当时的眼光,1968年10月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如此定性,“文革”“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是当时最权威的看法。那么,“以今天的眼光”又该如何看待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2021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今天的眼光”与“当时的眼光”,观察同一事件,差别何啻云泥!
如何看待历史人物?可以江青为例。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在“文革”中叱咤风云,她不仅是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负责人,也是名噪一时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这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的眼光,也是当时的官方称谓。然而,1977年7月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却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江青是“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决定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公报与判决书至今仍是我党的正式文献,当然反映了“今天的眼光”。对于江青“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难道还要恢复她在“文革”中的辉煌!
杂文圈的朋友见面,总是哀叹“杂文式微了”,“杂文低谷了”。其实,最近的两个杂文低谷之间,横亘着一座持续了30余年的杂文高峰。杂文当时的繁荣,是伴随着结束“文革”,解放思想的春风而来的。许多朋友经历过那个年代,许多重大事件记忆犹新。在当时,通过真理标准讨论,上下齐心,官民同慨,反对“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革”,许多禁区被打破,许多冤案被平反,许多偶像回到凡间。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显然是一个万物复苏、政通人和的解放与进步。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今天的眼光”,重新肯定了当年的历史决议,同时肯定了当年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这意味着真理标准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革”,实行改革开放,至今仍是正确的。

政治领域如此,文化领域同样如此。由于“文革”结束,改革启动,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和“中国第一圣人”的鲁迅,笼罩在头顶上的“三个伟大”、“一个空前”、“七个之最”的光环才逐步淡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在海外的论敌,著作得以出版(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鲁迅在大陆的论敌,终于脱离苦难(除李长之、徐懋庸、“四条汉子”中的周扬、阳翰笙、夏衍外,“文革”中罹难者不少);鲁迅生前看到的《鲁迅批判》,得以重新问世。在这种情况下,不许“以今天的眼光看鲁迅”,难道在政治上的“两个凡是”废除40余年之后,又要确立一个文化上的“两个凡是”?改革开放初期,茅盾在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时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2016年8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文化上的“两个凡是”并非无根之木,对于鲁迅的评价也是如此。
1925年,鲁迅把杂文定性为“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此时的鲁迅,一支健笔,横扫儒林,骂遍诸色。但以他的为人与为文,他自己决不可能既是论战的一方又兼任论战的裁判,而把自己划为“不许批评”的特区。鲁迅“容忍”《鲁迅批判》的出版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既是批评,就不能自设羁勒,自划樊篱,自相封神。不许“以今天的眼光看鲁迅”,这种思维不仅背离了坚持革新、反对复古的鲁迅精神,而且背离了尊重实践,与时俱进的真理标准。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他的作品体现了对黑暗中国的彻底批判精神,在他笔下,没有神坛,没有圣裔,没有权威,凡是阻碍国民之生存、温饱与发展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全集》第3卷,页47)对于今人,将近百年前的鲁迅,已是历史人物,也算古人了,他似乎专门针对奉承他、神化他的一些后人严厉指出:“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同上书,页18)
有名言称,“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不许“以今天的眼光”看鲁迅,不仅意味着禁止对鲁迅的批评和质疑,而且意味着只能以过去的眼光看鲁迅,这就是说,鲁迅还是“三家”“一圣”,还是“三伟”“七最”,就是说,鲁迅的作用是不能质疑的,鲁迅的思想是不能讨论的,鲁迅的作品是不能批评的。遗憾的是,这样的行径,体现的正是鲁迅一生与之抗争的文化专制。鲁迅说,“辩护古人就是辩护自己”,“辩护鲁迅”何尝不是“辩护自己”。由此可见,仍有一些人热衷于自建庙宇,自搭神龛,自塑金身,自愿朝拜,这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蹈常袭故,深闭固拒的思维方式,不仅代表了阻碍文化创新的守旧力量,这也恰恰否定了鲁迅一生挣脱文化羁绊的不懈努力。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