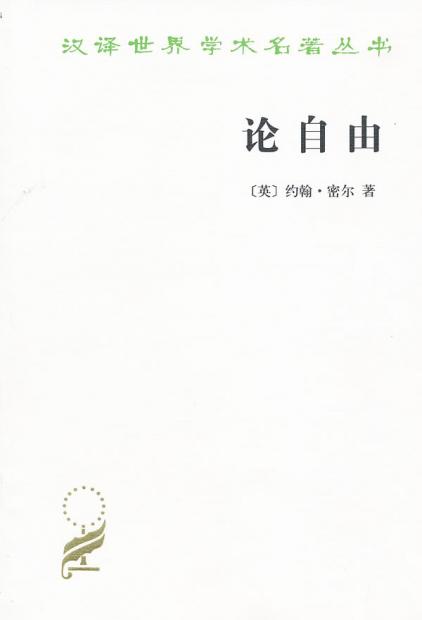
自由作为价值观,在我国,可谓命运多舛。自由被歪曲为“无组织无纪律”、生活上不拘小节,从而成为猥琐的自由主义;更多情况下,自由如同人权一样,被视同“西方敌对势力”的专用语。但在汉语里,“自由”毕竟是常用词,有时避无可避,只得采用皇权时代的“避讳”方式,将“自由”二字掐头去尾,在行文中写成“目田”,从而成为一枚青涩的梅子。
其实,自由作为人类追求的一种高尚美好的人生价值和生存境况,也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匈牙利人裴多菲的诗歌很有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他并非共产党人。1848年,与裴多菲大体同期的《共产党宣言》曾有一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50)这段话的内涵被称为“自由人联合体”。1867年,马克思首次把“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历史发展的最高目标:“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页95)1887年6月,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同上书,第21卷,页570)1880年3月,恩格斯仍然坚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书,第19卷,页247)至于这些蓝图,这些构想,比如在苏联,在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践,得到了实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而,正如前述,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自由始终是一个如同刺猬一样的麻烦话题。在经历长时期的冷落与敌视之后,近年来终于将“自由”二字列入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毕竟我们不会傻到把全世界所有的好东西都奉送给敌对势力。于是,满大街的核心价值观都不缺少“自由”二字。然而,这并不等于一些人真正认同了自由的价值,更不能说一些人真想付诸实施。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排除一些人用自由这样的好字眼装点门面,但从骨子里对自由的内涵极其敌视。一方面运用好听的辞令作大纛,一方面,拒绝这个辞令的真正内涵,其内里却是这个辞令的反面或侧面,也算是一种摆不上台面的统治术。只是担心搞不好,麒麟皮下会露出马脚。一些国人对自由的反对,也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论战中:一些拉大旗作虎皮的论者,往往无视论敌根本就不存在某种论点,为了批臭、整倒对方,而不惜无中生有,捏造罗织;对于论敌本来正确的观点,则推向极端,推向极致,无视对方的原文与本义,不怀好意地予以歪曲,予以篡改,不择手段地进行荒谬处理,将自己杜纂、编造的谬论强行按到论者头上,然后义正辞严地大声训斥。
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挂满了大街和小巷,一些人、一些媒体仍然蓄意对自由进行否定与歪曲,他们否定与歪曲的借口与逻辑仍然是有人鼓吹“绝对自由”,“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些荒唐的理由,无非是想通过对自由本身以及阐释这一价值观的有关人士的抹黑和扭曲,从而达到在广告上承认,在理论上否认;在表面上肯定,在实质上否定的卑劣目的。这种“无的放矢”、“画靶射箭”的行径,如同唐·吉诃德对于风车的宣战,是如此的可笑与可鄙。且不说国内从来没有任何论者发表过此种低级、卑劣的论点,甚至在“自由主义”的老巢里,数百年来,欧美学者早已对自由作出了界定与限制,所谓“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所谓“自由决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些原本已被前人否定与排除了的伪问题,根本就不在自由的范畴之中。国内一些人之所以提出这些极端和荒唐的问题,如果不是不学无术,就是别有用心,甚至是“司马昭之心”。
下面的文字,不是个人的撰述,纯属抄录性质。只是按照论点提出的大致时序,帮助读者梳理一下几百年来欧美学者是如何讨论自由这一概念的,看一看这些学者是如何否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绝对自由”的。
1690年,英国思想家洛克就曾指出:“处于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机关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机关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意志的管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所以自由不是像罗伯特菲尔麦爵士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各人乐意怎样做就怎样做,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而不受法律束缚的那种自由。’”(《洛克谈人权与自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页216)洛克是欧洲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不仅影响了后来的欧洲思想界,甚至影响了一些美国开国元勋。他的思想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得到了部分体现。300多年前,洛克就对“各人乐意怎样做就怎样做,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而不受法律束缚的那种自由”进行了否定与批判,从而成为后来的人们一致接受的思想。这个资料的意外价值,就是洛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实证,在300多年前的欧洲历史上,主张“绝对自由”的,实有其人。这也是我在多年的阅读经历中看到的唯一的、间接的例证。而这与国内一些批判者往往制造一些缺乏新闻五要素的、“莫须有”的“假想敌”根本不同。
1748年,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这样指出:“政治自由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如何确定某件事情“应该做”还是“不该做”呢?确定的标准只能是法律。他进一步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154)几乎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学者像孟德斯鸠一样,对世界各国的政治架构与政体产生如此深刻广泛的影响。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不仅成为美国宪法及美国政体的基石,也成为世界上许多民主政体的基本框架,当然也被另外一些国家视为邪恶,视为灾星。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对自由思想的阐述,几乎成为后世学者共同遵循的经典定义。
1762年,法国启蒙时代另一位思想家卢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页8)“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对于自由的哲理性描述广为流传。卢梭在这里所讲的道理,重点在于阐述法律限制自由的范围与程度。一旦超过必要的限度,自由就会挣脱羁绊以体现自身的价值。
1774年,英国的保守政治家埃德蒙·柏克认为,自由不是指纯粹的个人行为,自由问题涉及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正因如此,柏克特别强调社会自由的概念,他指出,社会自由“是那种与秩序紧密相联的自由——不仅依秩序和道德的存在而存在,而且随秩序和道德的消失而消失。”(《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95)1789年,他进一步阐释道:“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似乎每个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意志调节自己的全部行为。”(同上书,页105)柏林被公认为保守主义的先驱,他本人则是保守主义政治家。但在欧美语境里,保守与中国意义上的守旧、滞后不同,他强调经验,尊重人类理性;强调传统,反对怀疑主义。1790年,他说了一段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名言:“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审判官,这是建立公共社会的初衷之一,也是它的基本原则之一。”(同上书,页69)
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一宣言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宣言第一条明确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四条则进行了深入阐述:“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人权基本文献要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1)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文献的形式如此清晰地阐述了现代自由的概念。在这个经典式的自由定义里,人们得以明了以下几点:一、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二、自由是指人们可以做一切不损害他人的事;三、自身的自由必须以别人也享有同样权利为前提;四、自由的界限应由法律来确定。
1819年,法国政治思想家邦迪曼·贡斯当在演讲中指出:“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公民今天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涵义是什么?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34)在这次演讲中,贡斯当列举了一系列自由权利(因文字原因而节略),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指明了限制自由的两种因素,一种是法律制约,一种是专断意志。他对前者的肯定,对后者的否定是显而易见的。用法律确定自由的界限是公认的准则,而专断意志加之于自由,显然是对自由、对人权的干涉与侵犯,而这恰恰是专制主义的标志。
1859年,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一译穆勒)指出:“就一个人来说,他对于自己的事情,应当有自由欢喜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不应当以他人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为借口,而同样自由地欢喜怎样就怎样代替他人来做。”(《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124-125)这段话,我把它理解为“己之所欲,勿施于人”,可以看作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升级版。这种升级并不是主观随意的,完全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同上书,页66)这一理念之上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己”,既包括作为自然人的公民,也包括作为法人代表的官员。而往往是后者,“己之所欲”往往标榜宏大的名义如国家大业、发展大局等等,打着漂亮的旗号如长期受惠、整体利益等等,而“强施于人”。于是血泪强拆、毁苗改种的人间悲剧才会重复上演。密尔的《论自由》一书,与洛克的《政府论(下)》、罗尔斯的《正义论》并称自由主义三大经典。他在书中提出的“密尔原则”很著名:“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同上书,页10)
1842年3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页176)“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状态。鸟类和鱼类的自由边界,就是天的高度与海的阔度,而人民自由的边界就是法律。他这样指出,“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同上)马克思出生于西欧的普鲁士,一生活跃于西欧的学术和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西欧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正因如此,马克思关于自由的阐述,与西欧思想学术界关于自由的理念,不仅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在文字表述上也是相似的。
1945年,英籍奥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自由不仅要受到法律的限制,自由也应受到国家的保护,他指出:“我从国家那里要求的是得到保护;不光为我,而且也为别人。我需要对我及别人的自由加以保护。我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那些拥有铁拳和大炮的人支配。”(《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212)这个因预见到纳粹德国的威胁而避祸新西兰以后又辗转来到英国的犹太学者,提出这一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他也理性地指出,“当然很难精致地确定留给公民的自由度,使它不会危及国家保卫自由的任务。但是近似地确定其自由度却是可能的,这可由经验,例如民主国家的存在保证。事实上,大致确定(自由度)的过程是民主政治立法的主要任务。”(同上书,页213)他在论述中,曾经提供了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流氓抗议说,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他的拳头可以挥向他喜欢的任何方向;于是法官聪明地答道:‘你的拳头运动的自由受到邻人鼻子位置的限制。’”(同上书,页213)后来的学者们每当提及自由与法律时,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于这一比喻。
1962年,美籍俄裔学者安·兰德,由于其所拥有的哲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才能,她在论述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时,其观点一针见血,浅显易懂:“千万不要以为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样的话:‘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必管別人会怎样。’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光是他自己的,还有别人的。”(《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121-122)兰德曾经历过苏联的专制统治,她对权力如何干预个人自由,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她指出,“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的人:‘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想让任何人控制我的生活。我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我不想做主人,也不想作奴隶。我不愿为任何人牺牲自己,也不愿任何人为我牺牲。’”(同上书,P122)
如上所述,欧洲的先哲们对自由作出了清晰和明确的定义,这其中有硕学大儒,有政界要人,有革命导师,有两栖学者。他们有一个共识,都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为自由确定界限。不过,要说明的是,他们讲的法律,是指建立在人们的自然权利基础之上的、人民对于政治具有真实而充分的选择权的代议制机构制定的法律。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别。纳粹德国与暴政苏联所制定的法律以消灭自由、迫害人民、侵犯人权为宗旨,自然不在范围之内。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绝对自由”的生存状态,即使荒岛上的鲁滨逊、桃花源里的陶渊明,也同样受到所处时代、所处地域的自然经济条件的制约,即使没有政府与法律,他们也不可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恩格斯曾从人类起源的角度谈到人的局限,他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页110)自由无疑是一种权利,马克思认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同上书,第19卷,页22)可见,自由的界限,就自然历史条件而论,又不仅仅限于法律,只不过,这种界限需要法律确定而已。
在我国,经常有一种说法,不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也有人一厢情愿地远离政治,执着学术。然而,在一个学术空间十分逼仄的泛政治化社会中,任何学术问题都无可逃遁地陷入政治的漩涡。自由之类的问题,大概属于边缘问题,很难置于纯粹的学术平台来讨论,难免为某些习惯借端生事。讨论、商榷学术问题,至少应当遵循学术讨论、学术商榷的基本规则,唯我独尊,唯我独是,拿出文痞与学霸的架式,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无论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还是艺术问题,先上纲上线,凭空臆造对方根本不存在的荒诞离奇的谬论,强加到对方头上,将对方丑化、抹黑、妖魔化,然后如疯狗捕食,一拥而上,口诛笔伐,甚至棍棒交加,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理论自信,才能保证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样的行径几乎等同于学术流氓。这种作风在“文革”中司空见惯。“文革”谢幕40余年了,此类行径在媒体与网络上沉滓泛起,只能为我国的学术界感到悲哀。
欢迎关注“安立志”微信公号(anlizhi2015)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