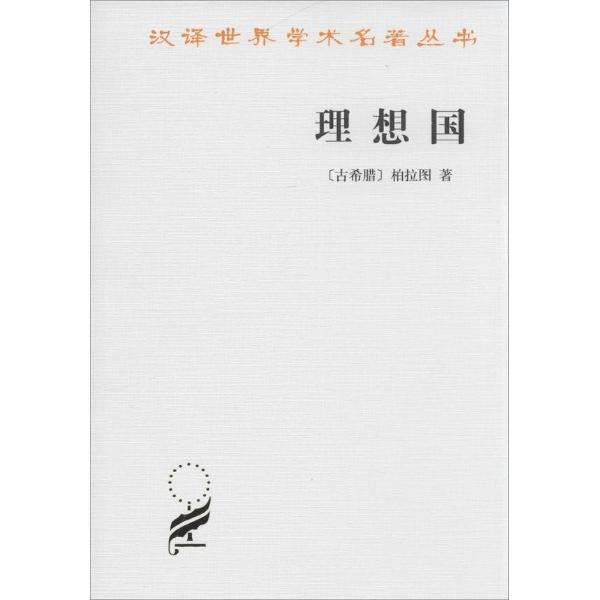
在前人的话语和文本里,曾经留下一些关于伟人、哲人、猛人的名词。这些人物是否真的祥云罩顶,是否真的光彩照人,是否真的高大威猛,不太清楚。在我的感觉里,伟人大抵是建立了不世功业的人,猛人至少是权倾一时的人物,只有哲人较少争议,这类人物往往是智慧与思想的化身。感觉的东西不太可靠,是否正确,自有方家校正。
其实,我对上述看法,也没底气,主要由阿克顿勋爵的那句名言引起,他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之后,紧接着写道,“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342)。本文涉及的几个人物,伟人、猛人是算不上的,是否哲人,或存争议。本文讨论的只限学术观点,称其为学人,谅无大错。其实这是一个丧气的话题,一些被视为思想家的人们,都是智慧与思想的化身,怎么忍心教唆统治者用谎言来欺骗他们的臣民?
柏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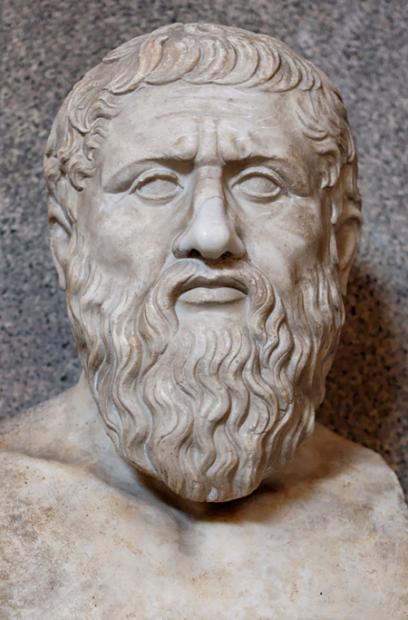
柏拉图(约公元前426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与中国的孔子差不多,被称为西方的孔子。柏拉图描绘了一个专制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国。他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王来统治,国民划分为护国者(统治者)、辅助者(士兵)和生意人(劳动者)三个阶级(《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56)。三个阶级的划分,被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辛辣地讽刺为“组成统治阶级的牧人和看家狗必须严格地和人类的家畜区分开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172)
虽然柏拉图强调城邦的统治者应当是哲学家,不过,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哲学家并不是热心的真理的追求者,相反却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他是有学问的人,是个圣者。”(同上书,页265)因此,“柏拉图所主张的就是学问的统治——智慧统治。”(同上)“智慧统治”是一种怎样的统治呢?
柏拉图把统治者比作高明的医生,把谎言当作治国理政的有效药物,“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它们都是作为一种药物使用的。”(《理想国》,页193)统治者作为国家和国民的医生,运用谎言和欺骗是“不得不”的选择,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而言,谎言是绝对必要的。而统治者的假话与撒谎,则完全是为了服务于“被治理者的利益”。
柏拉图指出,“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那么显然,我们应该把这种药物留给医生,一般人一概不准碰它。”(《理想国》,页88)他认为,欺骗与撒谎是统治者的专利,统治者具有专属使用权,普通人是无权撒谎的。“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它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同上书)在柏拉图的设计中,欺骗与撒谎,既有对外的功能,也有对内的功能。只要撒谎为国家,欺骗为人民,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即使是欺骗与撒谎,也要颁发正义证书。柏拉图这套理论似乎可以概括为“国家撒谎有理论”。
那么,怎样说谎呢?柏拉图出主意说,“现在我们或许可以用什么方法说一个那样的高贵的假话,使统治者自己相信(如果可能的话),或者至少使城邦里其他的人相信。”(《理想国》,页127)“首先说服统治者们自己和军队,其次说服城邦的其他人:我们给他们教育和培养,其实他们一切如在梦中。”(同上书,128)这就是统治者撒谎与欺骗所要达到的最佳境界。统治者们运用美妙动听的谎言欺骗自己的臣民与军队,这些浑浑噩噩的可怜的下属则幸福地生活在五里雾中。这一点,很像孔子主张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耐人寻味的是,柏拉图在这里使用了“说服”一词。统治者要说服民众相信其谎言,接受其谎言,准确地说,就是进行误导或欺骗。柏拉图考虑非常周到,“要让你们(统治者)的种尽善尽美”,即保持统治阶级的正统、传承与稳固,说了哪些谎,如何说的谎,必须严密封锁事实真相,“除统治者外谨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这种安排。”(《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页274)人民对这些谎言不相信怎么办?柏拉图告诫民众,“凡是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的事务都必须相信,那么就必须称它们是‘真实的’;除此再没有其他的真理标准。”(同上书,页264)国家散布的谎言都是“真理”,这样的谎言怎么可能是不“真实的”?
柏拉图的欺骗与谎言通过哪些渠道来实施呢?格罗斯曼正确地指出,柏拉图指的是“宣传,一门控制……被统治的大多数人行为的技术”。(同上书,页255)柏拉图的确是一位哲人,早在两千多年前,他已经意识到仅靠撒谎与宣传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于是他强调,统治者要“运用说服和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理想国,页279》)
黑格尔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尔的思想,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之一。
黑格尔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在设计一个专制主义政体——理想国,而黑格尔则是在维护一个专制主义政体——普鲁士王国。他写道:“精神……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本质上就是现在(1800年至1830年这30年,正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当政时期——笔者注):这必然寓示着,精神的当前形式饱含并超越了所有以前的步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93)说的明白一点,“现在的普鲁士”正是“自由的顶峰、堡垒和目标。”(同上书)波普尔对黑格尔的这一哲学论证愤愤不平,“黑格尔强令我们当作地上的神圣理念来崇拜的国家,只不过是从1800年到183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普鲁士,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同上书,页94)其实,不止波普尔看到了这一点,恩格斯更早地指出,“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页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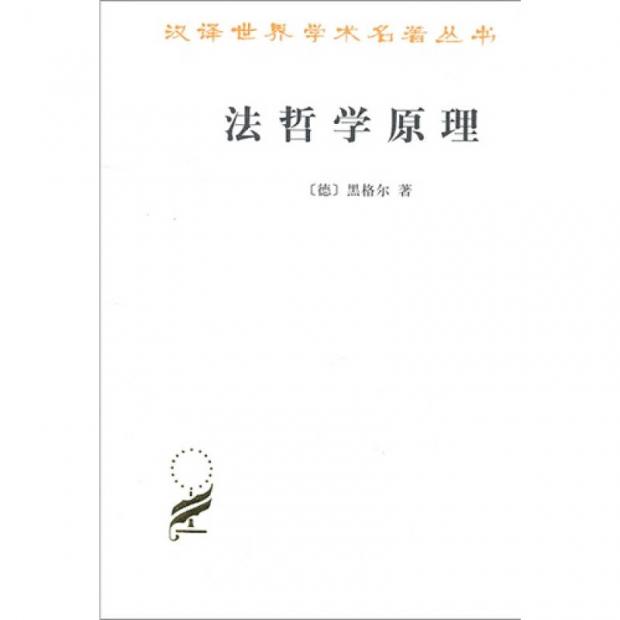
明人不作暗事。对于威廉三世这样一个至善至美、至高无上的君主,无论采取何种统治方式,包括欺骗,都是值得赞颂的。于是,黑格尔公开提出了惊世骇俗的问题:“一个伟大的天才曾经提出一个公开征求答复的问题:‘是否允许欺骗人民?’必须答说,人民在他们实体性的基础、精神的本质和特定性质方面,是不受欺骗的,但是关于人民获得这方面的知识的方式,以及关于按这种方式来判断他们行动和事件等等,他们却受自己的欺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333-334)这是一个典型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例子。意思是说,虽然从本质上讲,人民不应受到统治者的欺骗;但是,由于统治者的欺骗总是善意的,统治者灌输给民众的知识,或者灌输的方式或程序,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完全必要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百姓本来就是君主的臣民,接受君主的欺骗等于自我的欺骗。接受自己人的欺骗,也就不算欺骗。
他进一步指出:“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一切伟大人物的事。”(同上书,页334)在他眼里,臣民都是浑浑噩噩的群氓,群氓是发现不了真理的,只有“伟大人物”才能找到甚至发明真理。于是,这个“伟大人物”如同历史的灯塔,用他发现或发明的真理照亮了群氓的心灵,拯救了群氓的灵魂。由于这些群氓根本不具备识别这些真理是否赝品的素质和能力,因此,这个“伟大人物”即使向这些群氓兜售的都是荒诞与谬误,并用这些荒诞与谬误对群氓进行灌输,群氓也只能服从与接受。
群氓有可能对于什么是真理缺乏分辨能力,并不等于他们感受不到基本的善恶、现实的威胁与直接的损害。一旦这些直接善恶、现实威胁与直接损害迫在眉睫或者忍无可忍,同样可能形成“公共舆论”。“伟大人物”发明或发现了“真理”,他可能根本就不理睬、顾不上什么“公共舆论”,黑格尔非常理解地指出,“……谁(指统治者)在这里或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同上书,页33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脱离公共舆论而独立乃是取得某种伟大的和合乎理性的成就的第一个形式上的条件。这种成就可以保得住事后将为公共舆论所嘉纳和承认,而变成公共舆论本身的一种成见。”(同上书)那无非是说,“如果谎言成功了,那它就不是谎言。”(《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120)历史上其实也有这样的先例,谎言有时可以盖过“公共舆论”,成功了的“谎言”甚至可以转化成为“公共舆论”。波普尔对此概括道,“一旦持有这种观点,那么,就不会对宣传家的谎言和歪曲真理再有什么犹豫,尤其是如果它在推进国家的权力方面取得成功的话。”(同上书)
黑格尔是依附于普鲁士极权主义的哲学家,他非常清楚极权主义政体在建立与维系期间的所有行径或罪恶,黑格尔这种“为国家而撒谎”的哲学认为,他的“理性的绝对兴趣”在于维护国家“这个道德全体”,“在此间谎称英雄们的正当和功绩,国家的缔造者无论曾经如何残忍,他们都应该成为那种……可以毫不顾忌地对待其伟大的甚至是神圣的利益的人……”(同上书,页127),在这其间,极权主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蹂躏社会与民众,以至于尸骨累累,血泪斑斑。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完全是必要的,“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形式必然会践踏许多无辜的花朵;它必然要在自己的征途上把许多对象压得粉碎。”(同上书)这个意思,可以与我国作家鲁迅的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279)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晚于柏拉图很多,但早于黑格尔。此人在思想与学术上的建树不能与柏拉图、黑格尔相提并论。严格说来,马基雅维利算不上纯粹的学人,他与柏拉图、黑格尔毕生从事学术不同,15世纪末期他曾担任佛罗伦萨第二共和国的官员。马基雅维利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他的小册子《君主论》,这本书是他遭贬后献给君主的谄媚之作。此书在历史上的评价争议很大,有人称其为“独裁者手册”、“邪恶的圣经”。一些学者将其人其书与中国古代的韩非子及其著作《韩非子》相媲美。该书基本观点认为,一个君主要官运亨通,就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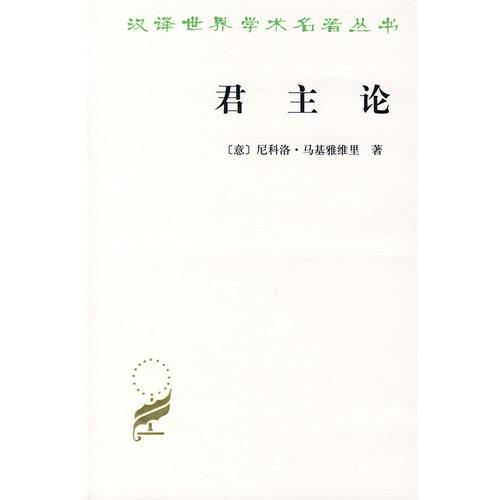
尽管这本书臭名昭著,在历史上却受到许多统治者的青睐。有资料称,英王查尔斯五世对《君主论》“爱不释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一直珍藏着《君主论》的手抄本。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在遭暗杀时,其身边遗物就有《君主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直把《君主论》作为每天睡前的必读书。曾经在欧洲战场所向披靡的拿破仑,最终在滑铁卢败北。打扫战场时,有人在他的战车中发现了一部写满批注的法文本《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建议君主“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83),并且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他的著名提问是,“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的多的。”(同上书,页80)马基雅维利给佛罗伦萨君主明确提出这样的建议,“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同上书,页84)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同上书)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要统治一个国家,只靠恐怖与暴力还不够,因为这只是体现了狮子的一面,还必须体现狐狸的一面,还必须要有欺骗与狡猾的一手,要善于伪装、善于掩饰、善于撒谎。君主虽然应当成为野兽,野兽毕竟不是什么好名声,因此,“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同上书,P84)马基雅维里毫无底线地告诫君主们:“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同上书)“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同上书,P85)他也试图解除君主内心因为残存的良知的各种顾虑,“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同上书,P94)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