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安·兰德的两本书
安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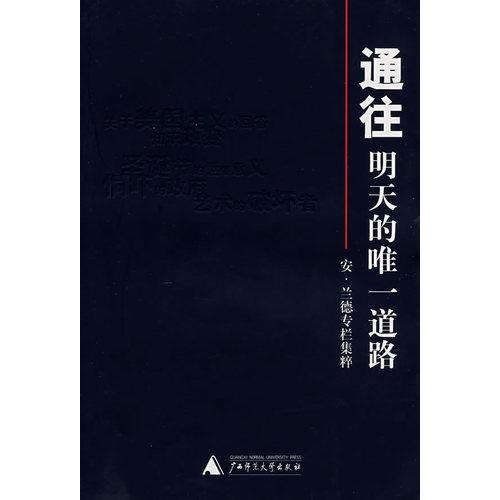
安·兰德(Ayn Rand,1905.2-1982.3),又译艾茵·兰德,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大学毕业后从苏联流亡美国,以其小说和哲学闻名于世。她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强调个人主义理念,主张理性的利己主义。她创作的小说《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成为国际畅销书,据说其发行量仅次于圣经。
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如何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一直被耳提面命。一当我接触安·兰德的有关论述,颇有新鲜之感。她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与传统理念与提法完全不同的认识维度与生活体验。
我并不全部接受她的观点,但回顾几十年的人生历程,旁观亲历,耳闻目睹,不能否认的是,安·兰德提供的许多视角都是切中肯綮的。因为所处环境不同,加之长期洗礼,一些坚持正统体制,拒斥不同思维的人们,对于她的表述,接受起来也许有些困难,但在理性与现实的结合上,她的论述与表达并不特别带有异端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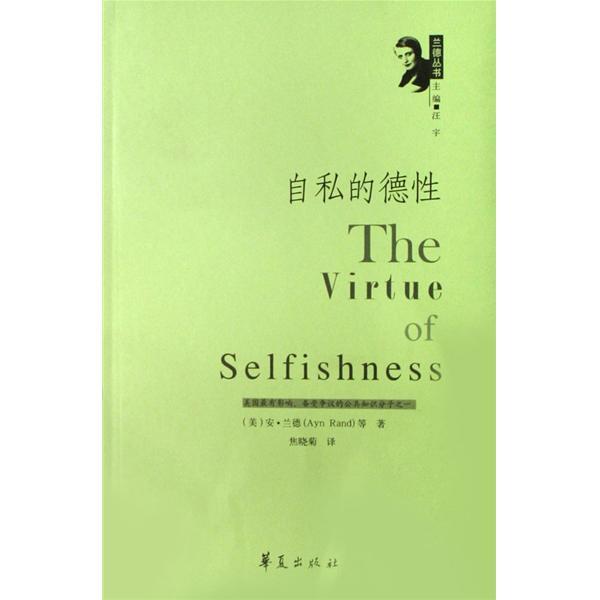
阅读安·兰德《自私的德性》(焦晓菊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以下简称《德性》)和《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下简称《道路》),按照我国传统的叙事习惯,从国家、集体、个人三个角度,对她的观点作点归纳与梳理。
国 家
在一些集权制国家,国家、政府、社会三个概念,往往混合使用而不易区别。安·兰德的大学时代在苏联渡过,运用这些概念时,也存在这类问题。比如,她曾指出:“此前的所有社会体系都把人视为满足他人目的的牺牲手段,并把社会本身视为目的。……此前的所有社会体系都认为人的生命属于社会,社会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个人,只有在社会同意向个人施予恩惠时,他才会拥有自由,而且社会会在任何时候撤回这种恩惠。”(《德性》,P91)这里的“社会”或“社会体系”,显然是指国家或政府。在这一点上,她不如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潘恩认为,“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P3)可见,在潘恩眼中,政府与社会是对立的。
马克思则对国家与社会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国家不在市民社会之内,而在市民社会之外,它只是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即受权在这些领域内‘照料国家’的人们来同市民社会接触。因为有了这些‘全权代表’,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变成了‘法定的’‘牢固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P305-306)在这点上,马克思与潘恩观点相近。反之,马克思认为,国家与政府在本质方面是一致的,他的表述十分简洁,“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同上书,P479)因此,按照马克思这一思想,本文在引述安·兰德关于国家、政府、社会的相关论述时,将国家与政府视为同一类概念。
安·兰德也曾对政府职能作过界定,她指出:“政府正确的职能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到暴力的伤害。”(《道路》,P123)在下面的论述中,她笔下的“社会”其实也是政府,“如果社会剥夺个人的劳动产品,或者奴役个人,企图限制个人的精神自由,强迫个人违反自己的理性判断;如果社会颁布的法令与人的本性需要之间存在冲突,那么,严格地说来,这就不是真正的社会,而是一群在制度化的帮派惯例下聚拢在一起的乌合之众。”(《德性》,P107-108)
这种看上去完全“正能量”的政府职能不是从天而降的,因为“政府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意味着政府不是统治者,而是公民的仆人或代理人;这意味着除了公民为了特定目的而委托的权利之外,政府没有其他权利。”(《德性》,P110)“自由国家的政府不是统治者,而是公民的仆人或代理,而且除了公民为特定的、具体的任务(保护公民免受武力侵害的任务,来源于公民的自卫权)而授予的权利外,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同上,P102)这样的观点并非资产阶级的论调,也并非特指“自由国家”,从本质上讲,与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时提出的“社会公仆”是同一概念。
尽管如此,许多先进的思想家都指出了国家的双重本质。英国学者波普尔指出:“国家权力从来就是一种危险的、却又是必要的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P207)马克思比波普尔更早地认为,国家“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3年,P56),是“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同上,P57)恩格斯则重复了潘恩的说法,把国家称作一个“祸害”和“废物”,他在为《法兰西内战》撰写的导言中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巴黎)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弃为止。”(同上,P13)可悲的是,一些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政权并非“新的自由的社会”,不但没有清除这些“祸害”与“废物”,反而变本加厉了。
安·兰德耳闻目睹了纳粹德国与苏联两个极权国家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她概括了这两类政权的共同特征:“政府没有成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却正在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政府不是在保卫自由,而是在建立奴隶制;政府没有保护人们免受动用武力者的侵害,却正在随心所欲地使用武力和高压政治;政府没有在人际关系中扮演客观工具的角色,却正在通过非客观的法律——随便哪个官僚都可随意阐释这种法律——创造致命的地下统治,那是无常和恐惧的统治;政府不是在保护人们免受奇想的伤害,而是在盗用不受限制地奇想的权力。……政府能够自由地做任何它喜欢的事情,而公民只有在获得允许之后才能行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是暴力统治的阶段。”(《德性》,P114)为什么是政府而不是别的事物“对人权造成了最大的潜在威胁”?原因在于“它拥有合法的垄断权来对那些在法律上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使用暴力。当政府不受个人权利限制和约束时,它就是人类最致命的敌人。”(同上,P96)从这一意义出发,她作出了一个结论性的判断:“人的权利有两个潜在的侵犯者:罪犯和政府。”(同上,P93)这其实只是事实陈述。
如何杜绝政府之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呢?安·兰德的思想是清晰的,那就是法律,也就是说,权力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她指出:“在正常的社会体系之下,个人合法地拥有随心所欲采取任何行动的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而政府官员在他的每一个政府行为中都受到法律限制。除了法律禁止的事情之外,个人能够做任何事;而政府官员除了法律允许的事情之外,他不能做任何事。”(《德性》,P109-110)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应该像没有个人喜好的机器人那样,把法律作为它唯一的动力。如果一个社会要成为自由社会,它的政府就必须受到控制。”(同上,P109)这既是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思想,也是美国政治家卡尔霍恩的思想。孟德斯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人们比较熟悉,卡尔霍恩防范权力的思想也很明确,他指出:“若不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防范,手握权力之人就会将这些权力转变为对共同体其他人进行压制的工具。对此类权力实施阻滞的东西,不论我们怎么称呼它,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也就是所谓的‘宪政’,且这种宪政是运用于政府的。”(《卡尔霍恩文集》(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P8)相对于卡尔霍恩,安·兰德只是美国政治理论界的晚辈,她所指出的,“设立政府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罪犯侵害,而编纂宪法则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政府侵害。”(《德性》,P93)“宪法是对政府而非个人的限制,它只对政府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作出规定,它不是维护政府权力的宪章,而是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侵害的宪章。”(同上,P114)当然,这些观点只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阐述或者对美国政治实践的概括,并非她的理论独创。尽管如此,安·兰德关于罪犯和政府是人权的两个“潜在侵犯者”的说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安·兰德有过苏联生活的经历,因此,她对于极权政治是十分警惕的。在她看来,所有的独裁政权,无论希特勒的德国,还是斯大林的苏联,不论其旗号如何,都是人民与社会的祸害。因此,独裁政权从根本上讲,都是一样的,根本没有“好”“坏”之分。试图进行这样的区分既是幼稚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在你讨论什么是‘好的’或‘坏的’独裁统治时,你就已经接受并认可了独裁统治的存在。你就已经接受了一个邪恶的前提——为了你的利益,你有权奴役他人。”(《道路》,P135)既然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都是一种祸害,那么,任何旗号的独裁国家,毫无疑问都是最坏的情况,当然也就是潘恩所说的“不可容忍的祸害”。安·兰德以其在苏联的感同身受,尖锐地指出:“如果独裁统治因为有了什么‘良好动机’或‘无私的动机’就可以名正言顺,那么这样的道德堕落实在令人发指。人类所有那些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拼命摆脱的残暴和犯罪倾向,如今又找到了一把‘社会的’庇护伞。”(同上,P136)
集 体
安·兰德的理性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是否定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这不仅体现为她的伦理观,而且体现为她的哲学观。她从伦理角度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伦理学是形形色色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教条,它使得个人服从于某种更高的权威,要么是神秘主义的,要么是平均主义的。结果,大多数政治体系都是同一种中央集权制独裁的变种,差别只在于各自程度的深浅。”(《德性》,P90)她从哲学角度指出:“任何群体或‘集体’,不论大小,都只是许多个体组成的。除了个体成员的权利之外,群体不拥有任何权利。在自由社会中,任何群体的‘权利’都来源于成员的权利,通过他们自愿的个人选择以及合约来获得,而且只是将这些个人的权利用于特定事业。”(同上,P101)有一次,她不无激愤地说:“任何群体活动学说,如果不承认个人权利原则,那么它就是暴徒统治或私刑合法化的学说。”(同上,P101)
在我们社会中,集体主义一向被供在神龛,受到无以复加的崇拜与强调。传统理论认为,集体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志。也有人将集体主义定性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内容之一,是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关于集体主义的制度设计与原则规定,在许多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这套传统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理论是严谨的,他们曾经从哲学上对何者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何者是虚假的(冒充的)集体主义,进行过深刻的辨析。
马克思主义区分真假集体主义的一个基本依据,是个人在集体中是否仍然拥有个人的自由权利。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假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P84)相对于这种虚假的集体,什么是真正的集体呢?作者继续说:“在真实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同上,P84)
这种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称为“虚假”、“虚幻”、“新的桎梏”的集体主义,安·兰德以通俗的语言信得过阐述,她指出:“集体主义认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他的工作、身体和个性都属于集体,集体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可以用任何方式任意对个人进行处置,所以,个人的存在需得到集体的允许,并且是为了集体而存在。”(《道路》,P117)这样的集体主义,并不是安·兰德的纯粹逻辑推理,而是真实的生活现实,它在苏联曾经大规模上演过。1929年,苏联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采取极其残酷的强制和武力手段剥夺所有不愿集体化的农民,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等大批生产资料被毁灭;农村出现了严重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百度百科)
我国1950年代的“集体化”,同样给中国农民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劫难。在集体化(合作化)过程中,曾因向往“耕者有其田”而参加革命的农民,刚刚到手的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农耕之家被强行瓦解,牲畜、农具被强迫“入社”;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铁锅被砸碎,不分男女老幼都被驱赶到“大食堂”。在这一过程中,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在各地肆虐。强行过渡的集体化终于导致了空前的灾难,1959--1961年,在没有重大自然灾害的和平年代,竟然导致3600万人被饿死。因调查这一悲惨事件而闻名海外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墓碑》的作者),于近日(2015年10月23日)获得瑞典方面颁发的史迪格·拉森奖,以肯定他对中国大饥荒的调查和报道。
这样的集体主义,显然背离了创始人的最初设想。创始人们指出,“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的无产者的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P84-85)可见,只有当本人控制了自身的生存条件,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并自愿地联合到集体之中时,这个集体对于个人来说才是真实的。而曾经发生在苏联和我国的集体化却是这样一幅图景:刚刚从旧政权下解放了的农民,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被政府强行控制,属于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被政府强行剥夺,并被强行驱赶进集体主义的羊圈里。这种野蛮地、强制地集体主义,如果仅仅定性为虚假的、虚幻的集体主义,显然太过轻描淡写。
集体主义者往往以虚幻的远景、虚假的成就欺骗世人。安·兰德指出:“只有思想被集体化的人才会在僵化的空想中认为:人类生命可以互相交换,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期望,为了公共科学、公共工业或公共音乐会可能给未出生者带来的所谓利益,牺牲几代活着的人是‘有道德’或‘令人向往’的事情。”(《德性》,P87)这些“可能给未出生者”带来好处的虚幻的东西,如同给人民画饼充饥,如同教人民望梅止渴,其实质就是要求每个个人交出其全部权利,并将这些权利集中到少数人、个别人甚至某个人手里。而这少数人、个别人或某个人却成为集体、大局、国家的化身。作为个人,上交了权利,就只剩下义务,于是他们只配作牺牲,而这些牺牲最终成为那少数人、个别人或某个人享用的供品。而那些向民众高唱美好愿景、宏伟理想的少数人、个别人或某个人,在将全体民众赶入集体主义的羊圈之后,他们自己开始享用由民众的义务和“无私奉献”构成的“供品”。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声明:“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因此,共产主义者并不……是要为了‘普遍的’、肯牺牲自己的人而扬弃‘私人’,——这是纯粹荒诞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P275)由此可见,那些要求人民“扎紧腰带”以保障“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竟然作为牺牲无数人命的正当借口,这样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肖子孙。
在集体主义的理念中,“整体利益”、“共同利益”的说法是司空见惯的。这些集体主义的口号,在日常生活中,变幻不定,花样翻新,不仅蛊惑人心,而且旨在洗脑。比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局部服从全局,部分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组织;“先治坡,后治窝”,甚至不顾基本的自然规律与语言逻辑宣扬十分荒谬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在这些人眼中,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集体与个人之关系,虽然美其名曰“对立统一”,但其骨子里将其视为对立关系,而且随时无条件地牺牲后者以服务前者。安·兰德不无极端地指出:“集体主义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告诉他们为了他们的兄弟牺牲自己的权利,结果,人们除了害怕、憎恨和毁灭自己的兄弟之外别无选择。”(《道路》,P129)这像极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作为集体成员的蚌和鹬,要么牺牲自己,要么牺牲他人结果只是为渔翁提供口中食。在这个集体主义机制里,鹬蚌兄弟为“自己”或为“兄弟”大公无私、慷慨奉献了,最后获利的一定是那个控制这个集体的“渔翁”——那少数人、个别人或某个人。
安·兰德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她以纳粹和苏联为例,作了进一步的解析:“在苏联和纳粹德国,老百姓做着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的肮脏勾当,互相监视,把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送到秘密警察手上,送进可怕的行刑室。这就是集体主义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结果,这就是空洞罪恶的集体主义口号的实际运用。对于缺乏思考的人来说,这样的口号确实是很动听的:‘公共利益高于任何个人权利’。”(《道路》,P128-129)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无法容忍后世的集体主义者如此荒谬地歪曲共同利益(普遍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马、恩二人指出:“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即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和所谓普遍利益,总是互相伴随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P273)普遍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同上,P276)他们进一步指出:“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突出的地方正在于:只有他们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同上,P275-276) 他们的思想很明确,二者的关系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这些普遍利益或者共同利益,总是由私人利益所产生或构成的,它们实际上等于私人利益的总和,没有私人利益也就没有普遍利益或者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这一全称肯定判断带有普遍的价值,可惜的是,以共产主义相标榜的后人中,已经没有这样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当然再不会发现这样的历史事实。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另一个立论基点。但在安·兰德看来,“‘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道路》,P129)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注释:“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同上,132)而这才是她的理性利己主义的核心。“极少数人”,哪怕只有一个人,也是人,也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少于任何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她指出:“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的所失。”(同上,P131)她以纳粹德国为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她指出:“德国有七千万德国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同上,P130)于是,作为“少数人”的60万犹太人,就成为“大多数”德国人的毒气室里的试验品。通过德国的例子,使我想起我国“文革”中那个著名的“百分之五”。这其实是毛泽东的一段著名论断:“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在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毛泽东列出了一道算术题,全国七亿人口,坏人占百分之五,那就是3500万,其规模相当于800万国民党军队的四、五倍。林立国“小舰队”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今天打倒一小撮,明天打倒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与“一小撮”的关系。而这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其自由、生命都是随时可以被剥夺的,他们根本不存在任何关于自己生死的权利。正如安·兰德所说:“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人多势众的群体(或任何自称可以代表多数人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来结束某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群体)的生命,个人的生存权利在那里是得不到承认的。”(《道路》,P118)实际上在“文革”那样的背景之下,结束某个或某些人的生命,根本不需要通过什么法律。
个 人
在我国,60岁以上的人们都经历过“文革”中的“斗私批修”。它是作为“文革”浩劫的一个阶段出现的。“斗私批修”是毛泽东提出的。他的亲密战友林彪解释说:“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林彪1967年10月1日在建国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这场斗争针对的并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古老的人生哲学,而是一场共产主义的洗脑运动。从“斗私”方面说,自私自利不行,公私兼顾也不行,大公有私不行,必须大公无私。这场斗争的极致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因此,与自私、自我、个人、个体有关的所有概念都被视为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这场斗争并非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影响所及,农村自留地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卖鸡蛋被当成资本主义残余。“文革”后期,中央报刊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端口号,以致于“文革”结束后《中国青年》杂志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竟然成为思想解决的口号。
安·兰德崇尚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即“一切人生来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以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P49)她指出:“人类权利的来源不是神律或国会制定的法律,而是同一律,A就是A,人就是人。根据人的本性,权利是人的正常生存所要求的存在条件。如果人要生活在地球上,他就有权运用自己的头脑,他就有权按照自己的自由判断来行动,他就有权为了自己的价值而工作并保留其工作产品。”(《德性》,P93)安·兰德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多么超前,她的《自私的德性》完成于1964年,其实,在1918年,也就是说在她的著作问世之前46年,毛泽东就曾指出:“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P152)至于毛泽东晚年背弃了早期的正确理念,则是另回事。安·兰德进一步强调,“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道路》,P131-132)她相信:“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善意,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有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都知道社会可以保护他的权利,而不是要毁灭他。”(同上,P129)
尊重个人的权利,必须从尊重个人的独立开始。安·兰德首先对人的独立性作出了阐述:“权利是对独立行为的认可。拥有权利意味着行动不需任何人的许可。”(《道路》,P120)“如果你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社会允许你存在,那么你就不具有拥有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外来的许可随时可能取消。”(同上,P120)“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必须获得社会的许可,无论你能否获得这样的许可,那么你都不是自由的。只有奴隶在行动前需要获得主人的恩准。恩准不是权利。”(同上,P12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要毁灭自由,就必须从毁灭个人权利开始。”(《德性》,P94)她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澄清,她指出:“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说什么‘杀人犯对社会构成犯罪’。杀人犯杀害的不是社会,而是一个个体;他侵犯的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属于个人的权利。……根本不存在‘对社会构成犯罪’这种情况,所有的犯罪都是针对具体的人,针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保护每一个个体不受到罪犯的伤害,正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公正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道路》,P124)
社会中的个人,并非身处荒岛的鲁滨逊,必然要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主义并非只以个人为中心,而无视他人的存在与权利。安·兰德指出:“一个人有活着的权利,但他无权剥夺另一个人活着的权利;他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他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利;他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他没有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权利(或对他人进行谋杀、抢劫或奴役)。”(《道路》,P121)“千万不要以为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样的话:‘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必管別人会怎样。’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光是他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同上,P121-122)“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的人:‘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想让任何人控制我的生活。我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我不想作主人,也不想作奴隶。我不愿为任何人牺牲自己,也不愿任何人为我牺牲。’”(同上,P122)
安·兰德客观主义哲学的合作者和她的情人纳撒尼尔·布兰登曾经写过一篇《伪个人主义》,收入安·兰德《自私的德性》一书中,其中一些观点,比较准确地诠释了安·兰德关于个人与个人主义的思想核心。他指出,“个人主义者是为了自己且依靠自己的头脑而生活的人;他既不会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也不会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德性》,P140)“个人主义者是理性的人。人的生命依靠的正是思考的能力和人的理性能力。理性是独立和自立的前提。”(同上,P140)“个人主义者基本的独立之处就在于他忠诚于自己的精神:他拒绝为他人未经证实的主张而牺牲他对事实的感知力、他的理解力和他的判断力。那就是智力独立的含义,那就是个人主义者的本质。”(同上,P140)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