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蜕变?
安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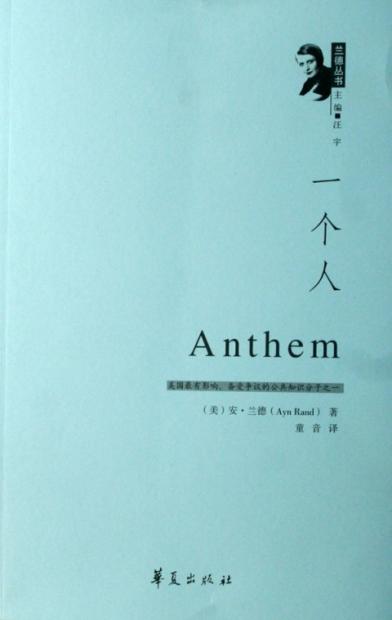
一
《一个人》(童音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英文版原名Anthem,《颂歌》),是一本不长的小说,作者是美国作家安·兰德。
这本书与《我们》(见拙作《我们只是号码》#53382874),有着太多可比之处。
从共同点来看——
首先说作者。两人都从俄国移居国外。《我们》的作者尤金·扎米亚金名声日隆时移民法国,最终客死巴黎。《一个人》的作者安·兰德大学毕业后流亡美国,加入美国籍。
其次是内容。两书都是反对极权主义、反乌托邦的虚构小说,主题都指向否定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应当指出的是,两书批评的对象都是“我们”。
再次是意象。两书都虚构了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托邦社会。书中人物都被赋予号码或符号式的称谓。而这作为消灭个性的特征,具有象征意义。
不同之处也很典型——
首先是创作时间。《我们》创作于1920年,于1924年在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一个人》创作于1938年,1939年在英国出版,在同类作品中,《一个人》甚至晚于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美世界》(1932年),仅早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
其次是作品的性质。《我们》是从科幻的、普遍的意义上批判、讽刺极权主义与乌托邦思想,并没有具体的指向。《一个人》的作者则明确宣布批评、讽刺的是苏联当局。她在回答关于“您是如何发现这个主题的”提问时说,“我在苏联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181)
再次是作者的命运。《我们》的作者扎米亚金不堪忍受国内政治压力,被迫移居国外后,由于创作资源枯竭,此后再无影响。《一个人》的作者安·兰德则在流亡国外之后,才开始了创作历程,不仅小说创作取得极大成功,而且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客观主义。
在我看到的材料中,没有关于安·兰德创作《一个人》时在主题、情节等方面借鉴《我们》的介绍。但我相信,关于联众国与乌托邦、绿墙与未知林、号码与符号这一系列意象的相似,并非偶然,这其中一定存在着后者向前者的借鉴过程。
二
《一个人》描写的社会,没有国名。从其情节来看,这并非一个处于遥远未来的后文明社会,而是一个被时代甩在后面很远的“荒废”了的国度。这从两个方面可以印证:这个国家曾经有过一段繁荣的过去,但这段历史被当局确定为“不宜提及的年代”且只要提及就是犯罪。书中发现了那个年代的地铁隧道遗址,就是证据。而如今这个国家用来卖弄的最新科技发明是:如何用蜡和细绳制造蜡烛;如何制造玻璃以遮挡风雨。由此可知,这曾经是一个经济、科技比较进步的现代社会,只因逆潮流而动而倒退到经济、科技比较落后的前现代社会。这种发展路径连中国的桃花源都不如。桃花源里的人们,“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虽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毕竟没有从秦倒退回商周时代。
这个社会奉行的原则是——“我即众人,众人即我。无有个人,‘我们’为大,个体极微甚小,此为真理,永世不变”。这个社会,没有个人、只有集体;没有自由,只有奴役。为贯彻这一方针,这个社会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都要整齐划一,保持一致;任何个性都在必须消除之列,而且不能允许存在任何差别;社会成员不得独立行动,禁止任何社会成员产生“私心偏爱”;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抹去对“不宜提及的年代”的任何记忆,一切都要从“伟大重生的年代”开始。为保持高度统一与一致,这个社会实行了最严厉的控制与惩治,甚至人们产生不愉快情绪也是犯罪。
从这样的社会现状出发,所有社会成员都不允许有姓名,只以一个口号加一串数字来区别,每个人手腕上戴着一只铁制手镯,上面刻着每个人的符号。男主人公的符号是“平等7-2521”,女主人公是“自由5-3000”。此外还有大同2-9913、集体0-0009等等,如同监狱中称呼囚犯。作者安·兰德解释过这些名字的含义:“我用的这些数字套用电话号码,并以集权主义者的口号作为前缀。”(《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P179)在这个社会里,由于否定个体价值,否定个性存在,因此,人们根本不知道还有“我”这样一个概念,无论第几人称如“我”“你”“他”,都要使用复数如“我们”“你们”“他们”。
这些符号从婴儿之家到学生之家,从幼年到成年,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有的只是国家与社会。比及成年,他们如同“螺丝钉”,职业委员会如同“螺丝刀”。“螺丝刀”把这些“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没有理由,没有条件,天才可能被安排去淘粪,白痴可能被指定当领导。职业委员会五名成员如同古板僵硬的大理石般坐在台上,学生们一个接一个走到他们面前,由他们派定学生一生的职业——“木匠”、“医生”或者“领导”。这种指定无论如何荒谬,学生也要举手宣誓:“人民同志的意志实现了!”“平等7-2521”走到跟前,一块“大理石”用手指了指他说——“扫街者”。这个具有科研天赋的年轻人不由分说成了一名终身的清洁工。
这个社会的成员没有姓名,却有性别。法律规定,只有到交配时期,男人才能想女人。交配时期在每年春天(这使人想起我国俗称的“思春”或“叫春”),所有年龄超过20岁的男性和年龄超过18岁的女性,都会被送到城市婚姻大厦住一晚上。优生联合会为每个男人指定一个女人。每个人都会被送去交配两次。这种交配,并非婚姻,亦非爱情,任务只为造人,即劳动力再生产——一般每年冬天孩子出生。但是,女人们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孩子也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原以为,这只是安·兰德的文学虚构,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却提供了一个现实佐证,“红色高棉在太多的人死于清洗和饥荒后急于增加人口,宣布每月的第一天、第十天和第二十天是交配的日子,是夜已婚夫妇被允许、也是被强迫做爱。警卫就在半透明的竹帘外巡逻,证实夫妻们在交配。但是许多夫妻因为白天的强迫劳动过于疲劳而无法做爱,只能做出虚假的运动并伪造出声音……”。(《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毕竟这里还有婚姻。
“扫街者”平等7-2521与他的两名工友——高个儿青年国际1-5537和缺心眼儿的联合5-3992,无意发现了“伟大重生年代”之前的一个地铁隧道。这个“不宜提及之年代”的遗址证明,“成百上千年之前的人类掌握了现在的我们已然失落了的智慧,对天地间的一切秘密了然于胸。”平等7-2521在这个秘密空间里,利用捡来的废品、偷来的书稿进行学习和实验。当然,这一切都是犯罪。经过多次试验,他终于用金属线和玻璃等物品制成了一个能发光的新装置,这是一种新能源——电。他准备将这个发明提交给在当地举行的世界学者大会。没想到,他因擅自离岗被带到教养拘留所,挨了一顿残酷的皮鞭,并关进牢房。
平等7-2521成功越狱,仍然不忘手捧着他的玻璃盒子,径直走进举行世界学者大会。他刚刚表明“扫街者”的身份,就被学者们下了逐客令。尽管他极力表白:“我们把天空的能量献给你们,我们献给你们的是世界的钥匙!收下它吧,……让我们共同工作,利用这种能量减轻人民的劳苦。把手中的蜡烛和火炬都扔掉吧。”他的奉献是无私的、热诚的,然而,却被冷酷无情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多种多样:“一个扫街者,你们怎么敢认为自己能做出比打扫街道更有利于人民和事情?”“你们这种清洁臭水沟的人……怎么敢自行思考而不和同志们保持一致?”“蜡烛对人类居功至伟,……蜡烛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遭损毁。”“如果这种能量能减轻人民的工作负担,那么它就是一项大罪恶,因为人们如果不为其他的兄弟同志们操劳,也就没有存在理由了。”这些学者们恼羞成怒,不仅要毁了这个发明,而且要使发明者尸骨无存。危机关头,平等7-2521夺路而逃,逃往没有人迹的未知林,始终抱着他的玻璃盒子。
农民之家那位漂亮姑娘自由5-3000和平等7-2521一样,他们经过几次交往,勾起了灵魂深处潜藏的人性和真挚的爱情,他们相互赞美,相互倾慕。小伙子把自由5-3000称为“璀璨者”,姑娘把平等7-2521称为“不可征服者”。平等7-2521被迫逃亡之后,自由5-3000闻讯,也追随平等7-2521来到未知林。他们为生存而探险,为前路而摸索。他们一边逃亡着,一边怀疑着,“一切由众人决定的都是善,一切来源于个人的都是恶”。自打出生就接受这样的教育,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们不知这差错是什么。
他们在未知林里发现了“伟大重生年代”之前的房屋、书籍、衣服及其他物品。回顾、观察、对比、思考,他们开始明白,观察世界是我的眼睛,倾听万物是我的耳朵,思索不止是我的思想,进行选择是我的意愿……。他们一直想知道万事万物的意义,而“我”就是意义。他们终于挣脱了“我们”这个丑陋的、空洞的外壳,最终完成了蜕化,真正成为美丽的、自由的、飞翔的精灵——“我”。找到了自我,也就找到了人生目的。平等7-2521从他找到的第一本书中看到了“我”这个词,他告诉自由5-3000:“人不应该没有名字,有过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以此区别于其他所有人。”男方不再是平等7-2521,借用从天神那里偷来光明撒播人间的故事,从此他被叫做普罗米修斯。女方也不再是自由5-3000,借用万物之母的故事,从此她被叫做盖亚。
三
安·兰德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家,她同时也是哲学家。《一个人》的情节设计、人物塑造,没有多少出彩之处,甚至有些松散与疏离,然而,这些情节与人物诠释的是全新的思想。她在《致新知识分子》(冯涛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我经常被问及我首先是位小说家还是位哲学家,回答是两者皆是。”她赋予小说家的使命是,“他的作品要么是对某种已经存在的哲学观念的个人化表现,要么就要创作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框架。”《一个人》显然是为了体现她的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她在《致新知识分子》一书中选择了这部小说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有的是小说人物的对话,有的是小说作者的独白,大致都属于她的哲学思考——这可以视为由“我们”蜕化而出的“我”的表白。不过下面的引文仍然依据《一个人》的文本。
“什么样的灾难摧毁了人们的理性?什么样的鞭子携带着羞耻与服从鞭打他们的膝盖?是对‘我们’的崇拜。人们接受这种崇拜之后,几个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大厦轰然倒塌,这个建筑物的每一根横梁都来自‘某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P87)
“我既不是别人想要到达的终点的过程,也不是供人利用的工具,不是供他们驱使的奴隶,不是包扎他们伤口的绷带,不是他们祭坛上的牺牲。”(同上书,P79)
“‘我们’这个字眼……永远不能放在首位,否则它会变成一个怪兽,变成大地上一切恶的源头,变成酷刑和无法戳穿的谎言的源头。”(同上书,P80)因为,“在那样的世界里,堕落者偷来良人的美德,懦弱者盗用强者的力量,蠢人夺取智人的智慧。”(同上书,P80)
“不过现在我已经和这种堕落的信条脱离了关系。已经和那个怪物‘我们’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为奴隶制,为肆意掠夺,为不幸、虚妄和羞耻服务的字眼。我看见了神明的脸容,——这个神明的名字只有一个字:‘我’”(同上书,P81)
环顾世界,当今时代,还有多少尚未蜕化的“我们”?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